海瑞是明察秋毫的的清官?明察秋毫起码谈不上
首先,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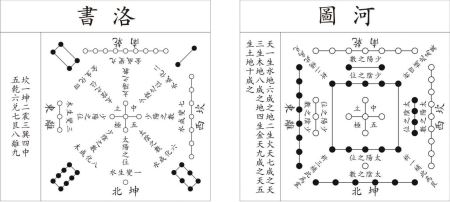
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
(《海瑞集》)从封建道德观来看,它的所谓断案标准完全符合封建礼法要求。
然而,从法治精神来看,无论屈谁都是不公平的。
海瑞与封建社会的另一个清官形象——的差别十分明显。
一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个是调动各种刑侦手段一查到底。
在执法的严肃性上,海瑞远不如包拯。
其次,在对待契约问题上,海瑞不顾当时的国情,片面强调要式主义,致使法律的执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明代法律规定,贷款的利率不超过三分,不论借款时间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
法律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占有,五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
(《大明会典》)法律的规定是十分明确与严格的。
然而,到了海瑞那里,则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这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
因为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
这样一来,不知有多少人在海瑞的貌似公平的判决下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法律在海瑞的手里被人为地扭曲了。
海瑞自己也承认,他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1/20。

(《海瑞集》)结果,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搞乱了。
最让人诟病的是海瑞的家庭悲剧。
明人姚叔祥的《见只编》上,记有一条有关海瑞的材料,说:“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
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
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憧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
女即涕泣不饮啖。
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
”这个故事用白话来说,就是海瑞有个女儿,年方五岁,正在吃糕饼,海瑞问她,糕饼是从哪来的,女儿回答说:是某个仆人给的。
海瑞生气地说:“我女儿怎么能随便吃仆人的糕饼?你不是我女儿!如果就此饿死,才称得上是我女儿。
”小女孩就哭着不吃东西了。
家里人想方设法要她吃,她坚决不吃,一个星期后,女孩死了。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但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的人,却并不一定这么想。
在他们眼里,海瑞的“怒”,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为的是让女儿从小就懂得尊严;而女孩的死,则昭示着有其父必有其女的道理,她用幼小的生命挽回了自己的尊严。
如果说这个材料让我们感到海瑞的的话,另一件事则恐怕更有损于我们心目中海瑞的形象。
明人沈德符撰的《万历野获编补遗》说,房寰曾经疏攻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

就是说,海瑞的政敌曾攻击他私生活有问题。
海瑞一生中,先后收为妻妾的妇女,计有、、、、等多人,让人吃惊的是,他曾两次出妻,其中第二任妻子在结婚一月即被逐出家门,第三位妻子则于1569年不明不白地死去。
海瑞的不断纳妾,造成了他年“已重而妻方艾”的局面。
尤其是他在花甲之年还纳了两个年轻美貌的侍妾,妻妾相争,有二人同日自绕,成了言官疏参、时人讥评的话柄。
这就不能不使人对海瑞的为人、尤其是对待女人的态度大存疑问。
即使按封建的婚姻道德标准来衡量,海瑞的也是不可取的。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海瑞的另一个政敌、吏科给事中戴凤翔曾疏参“瑞出京师,用夫三十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人。
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救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
虽柴烛亦取足,有司抬轿径人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责三十,尚不愧悟!”这虽然来自对手的攻击,但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美化古人是中国文学家的惯用手法。
但由于普通老百屋及乌,会不自觉地将古人的一些劣迹以及错误的思想一并吸收、弘扬,这就导致我国现代法治思想难以流布。
人们在舞台人物的唱词中汲取到了太多错误的法制观念,以致于在今天的法庭上仍能听到老百不时运用古代清官的思维逻辑来判断眼前的纠纷。
海瑞毕竟是个封建官僚,或者说,海瑞毕竟是个凡人,他不可能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高大完美、一心为公、爱民如子。
保证官员廉洁的关键条件,不仅在于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更应该是法律制度,这是探讨海瑞现象所给予我们的深刻示。
其实对于海瑞的讨论,宣传海瑞的形象其实也只是在于告诫我们一个国家是需要清官,清官的意思是要敢于说真话,敢于为这个国家的利益为重,其实也许它并没有去表现一个像圣人一样的人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