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真实灵异事件簿_白夜灵异事件簿
【帆叶网探索分享关于古尔纳,张丽相关的知识】
2000年8月,上海发生了一件惊悚怪事:一个农民在挖地时发现一具不腐古尸!当时正值夏季,古尸居然通体冰凉,犹如刚从冰窖里捞出来……8月5日这一天,松江区华阳镇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 *** ,报警的人说话哆嗦,语无伦次,明显是被“吓”得不轻!
原来,在一处平整土地的工地上,挖土机挖出了一具漆黑的棺木,由于机器的作用力,棺材盖子已经被掀开。
在场的人有胆子大的,上前往棺材里一瞧,吓得连连后退!只见棺材内赫然躺着一具没有腐烂的尸体!
民警接到报案,也不敢怠慢,赶紧到了现场。
穿过围观人群来到工地中央,他果然看到一具身穿古代服饰的古尸,面朝下趴着。从服饰来观察,这应该是一具古代男尸!
当上海市松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杨坤来到现场后,胆大心细的他上前用手轻轻触碰了男尸的皮肤,心中却突然“咯噔”一声!
“怎么这么凉?……”杨坤心中一惊,因为刚才他的指尖触碰到尸体后,一股冰窖般的凉意一下子袭来!
可现在是8月份啊,正值上海最热的时候,室外气温高达三十多度。这古尸居然可以做到体表温度“冰凉“?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虽然心中起疑,但是杨坤还是淡定的检查着古尸身边的其他东西。接着,一个戒牒[jiè dié] 被找到了。
什么是戒牒呢?戒牒也叫作“度牒”,古代的时候一般由尚书省下的祠部颁发给僧人,用于证明他们的身份,类似身份证的作用。
僧侣们带着戒牒云游四方时,遇到寺庙前去叨扰就需要出示戒牒证明身份。
古尸身上发现了戒牒,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一名僧人。
杨坤还从戒牒上找到了此人的信息:戒牒持有者名叫杨福信,戒牒是明代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颁发的,距今500多年了。
也就是说,这位名叫“杨福信”的僧人,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古人!
古尸没有什么豪华的墓葬措施,就是一口棺材掩埋,掩埋地是潮湿多雨的江南,他是怎么做到“尸身不腐”的呢?
更怪异的是,正值炎炎夏日,古尸体表居然异常冰凉,这又是为何?
疑问还未找到答案,不过墓主人几件简单的随葬品已经清理了出来。和预想的一样,没有金银器物,只发现了一个武士木头人俑和一杆铁头标枪。
这两样东西,似乎将杨福信的另一个身份逐渐表明——练武之人!
为了弄清楚这杆木制的铁头标枪到底是不是兵器,考古队请来了国家**总局武术研究院专家康戈武。
康教授发现这杆木制标枪和一般习武的枪不一样:枪头是圆铲形的,在古代兵器里没有类似的枪,可以判定这杆枪并非兵器!
在实验室对杨福信的尸体进行进一步研究后,考古专家们发现,尸体皮肤湿润、柔软有弹性,有些关节居然还能活动。他的死亡年龄大约在75到80岁之间。
在检查中,专家还有一个重大发现:杨福信的手掌比较大,特别是手掌的骨骼比一般人要大。这一特征进一步说明杨福信生前很可能会武。
陪葬的武士木俑、木枪以及超大的手掌,都说明杨福信可能习武多年。既然是武林中人,他的尸体不腐,难道会与江湖传说里的一些秘术有关?
为了探究这具古尸的不腐之谜,专家们还在继续寻找线索。
在采集了尸体的毛发、内脏组织等进行化验之后,发现杨福信的体内重金属元素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属于正常范围以内。
这个结果表明,此人生前并未服用任何重金属相关的“防腐剂”,比如水银之类的。
接着,专家从棺内的组织液来观察,杨福信的“自溶现象”很充分。体内细胞在他死后就开始了分解。
既然如此,在接下来的500多年里,在细菌的作用下早应该把他变成了一副枯骨。可是,他的尸体却一直完好地保存到了今天!
这些检测中都没有找到尸身不腐的原因,专家们最后想到的墓葬的原始环境!
由于刚到现场时,墓葬已经被挖土机破坏,所以大家没有过多关注。加上开棺之后,棺内还有棺液,于是所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墓葬密封性能并不好……
直到现在他们才发现,杨福信的棺椁用的是江浙一带明代墓葬常见的“三合土”密封。所谓三合土,是用糯米熬制成浆,再加上石灰、黄土,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与现在的水泥相类似。
杨福信的棺椁底部比较薄,导致地下水长年累月之后侵入棺内形成了棺液。不过,这些地下水干净清澈,没有细菌,无形之中将尸体包裹其中,隔绝了外部空气。
加上外部密封性能非常好的三合土,便形成了一个“真空胶囊”,将杨福信的尸身完美包裹,直到五百多年后被人挖出……
一生信佛的明代古人杨福信,虔诚之心也许真的感动上苍,得以五百年尸身不腐,算是修成了正果……
可是,为何炎炎夏日,古尸却如冰窖般冰凉?没有解释……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一:现代真实灵异事件簿txt
对于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所有人的脑袋里都打着同一个问号
这个人是谁?
一个“无人知晓”的诺奖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
发于2021.10.18总第1016期《中国新闻周刊》
“拜托,别瞎扯了!不要烦我。”
接到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的 *** 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正在泡茶,对于自己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他以为只是有人在搞恶作剧而已。直到十几分钟以后,诺奖官网主编亚当·史密斯再次致电,他依然在电脑上确认着这件事的真实性。
不相信这个结果的,其实不只古尔纳自己。在早先甚至历年的**赔率榜和全球媒体预测中,他的名字都从未被提及过,何况自1986年沃勒·索因卡以来,诺奖就再也没有颁给过非洲**作家。作为客居英伦的移民作家,古尔纳在英国的名气远远不及“移民三杰”石黑一雄、奈保尔和拉什迪,英国之外的地方更是鲜有人知,美国专门追踪实体书和电子书销售数据的NPD Bookscan数据显示,其作品《抛弃》自2005年在美出版以来,在向该服务报告的销售点只卖出了不到2000本,甚至公布结果当天,诺奖官方发起的投票尴尬地显示,超过九成读者都没读过他的文字。
尽管古尔纳此前凭借《天堂》《抛弃》《海边》入围过布克奖、惠特贝瑞图书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的名单,却并未真正摘得哪顶桂冠。正如他的
而在中国,除了一本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选集》中收录过其两个短篇,再没有任何作品被翻译为中文,以至于准备报道的媒体在第一时间都无法准确写出他的译名,所有人的脑袋里都打着同一个问号——这个人是谁?
比起作家,他更出名的角色是评论家
临近东非大陆的印度洋西部有一座小岛,名为“桑给巴尔”, *** 语意为“**海岸”。公元5世纪前后,躲避战乱的 *** 半岛居民开始向这里移民,到1505年基尔瓦王朝被葡萄牙舰队击溃,这里已经充分 *** 化,并由土著文化与 *** 文化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斯瓦希里文化。
1948年,古尔纳就出生在这座小岛上。彼时的桑给巴尔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中,因此说着斯瓦希里语的古尔纳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习英文。在他15岁那年,桑给巴尔经过数次抗争,终于宣告独立,成为苏丹王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少年古尔纳的厄运却从这里开始了。
1964年1月12日清晨,在非洲大陆**和设拉子人组成的反对党——非洲设拉子党——的动员下,600~800名革命者袭击了警察部队并夺走武器,前往桑给巴尔镇推翻了仅仅成立一个月的苏丹王朝及民族党和桑奔人民党组成的联合 *** 。由于英国殖民者离开这里时,留下了一个少数 *** 裔统治多数非洲裔的政治结构,因此革命者建立的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随即对岛上的 *** 和南亚裔平民进行了报复,数百至两万人(人数尚有争议)被屠杀,许多 *** 和南亚妇女遭到 *** ,财产被洗劫。
在古尔纳的回忆中,这场暴乱是可怕和令人震惊的。2019年,他面对《Wasafiri》杂志的采访时说到:“我那时是一个学生,我们学校被关闭了,我们大部分的老师是欧洲人,仅仅一个月时间,他们就不得不按要求离开。到处都是枪,革命以前我们从没见过枪,哪怕是在警察身上。现在一个带着枪的人可以走进一个小商店,就像一只野生动物走进去一样。”
面对充满艰辛、焦虑、国家恐怖和蓄意羞辱的生活,古尔纳在18岁时选择离开桑给巴尔岛。他在肯尼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于1968年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此后十余年,他都未曾再回过故土,直到1984年才在父亲去世前不久归乡见了最后一面。
1976年,古尔纳从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学院毕业,获得伦敦大学教育学士学位,随后在肯特郡多佛市的阿斯特中学任教。1980年,他开始执教于尼日利亚的巴耶罗大学,同期攻读英国肯特大学博士学位,并于1985年进入肯特大学任教。这份教职成了他终身的事业,直到退休,古尔纳一直在肯特大学担任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从事与非洲、加勒比、印度等地区相关的后殖民文学研究。
从1987年开始,古尔纳还一直 *** 《Wasafiri》杂志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副教授张峰,自2010年左右便开始对古尔纳的文学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古尔纳的作家身份之所以不太被人熟悉,正与其学者和评论家的身份有关。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多重角色可能是一个好事,但同时也会淡化他的作家的这种角色,在英语文学研究界更多是把他看成一个评论家。”这并非孤论,《新共和》的专栏作家亚历克斯·谢泼德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古尔纳最出名的可能是他作为评论家的工作。”
或许就算古尔纳本人也不会对此提出太大异议。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过:“当你从事你的职业,并且到达更高的级别,也就不得不承担更多与教学、书籍等等无关的机构职责,这就是矛盾所在。也就是说,你的脑子里充满了其他东西,很难找到空间来安放那些你感兴趣的东西,比如写作。”
难以抗拒的记忆与甩不掉的孤独感
事实上,对于古尔纳而言,从事写作原本就是一件偶然之事。2004年,他在《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在桑给巴尔生活时并没有打算成为一名作家。“在那之前我写过东西,虽然彼时我还是桑给巴尔的一个学生。但那只是闹着玩的,为了**朋友和在学校的讽刺剧中表演,不过是心血来潮或者打发时间或者炫耀。我从不认为那是在做什么准备,也不觉得自己要立志成为一个作家。”
真正促使他拿起笔来的,是到英国后产生的一种被生活抛弃的失重感。这是异乡人和无根者才有体会的感受,对外部世界的陌生以及自身与周遭无法弥合的差异,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你已经失去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渐次累积的漠视、孤立甚至侮辱,则不断勾勒并强化着内心的某种记忆——它来自失去的地方和生活,或者仅仅是一个与现实不同的地方、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
当然,一切的开始并未如此思路清晰。最初的古尔纳只是漫不经心地写着,在日记中写下关于家的小片段,然后是其他人的故事。后来他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在凭记忆写作,那种记忆如此生动又难以抗拒。于是他正式交出的第一部作品,取名就叫作《离别的记忆》,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试图摆脱故乡的困境,却最终历经羞辱后回到了破碎家庭的故事。
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出走,多少掺杂着古尔纳自己在英国的最初岁月的不适。到了第二部作品《朝圣者之路》,他则开始尝试寻找和解的可能性。流浪到英格兰的主人公达乌德,努力隐藏着自己过去的一切,最终却还是在一份异性之爱面前讲述了那些创伤的记忆。**结束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达乌德蓦然发觉原来自己曾反抗的那些东西,竟然散发着触手可及的美。
1990年,古尔纳写出了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角、也是唯一一部主角出生在英国而非桑给巴尔的**《多蒂》。作为生长于充满种族歧视的1950年代英格兰的**女性,多蒂既在这里感到无根,又因为母亲的沉默而与自己的家族历史缺乏联系。她试图通过书籍和故事创造自己的空间与身份,并且逐渐在探索中发现自己的名字背后隐藏着一段悲惨的家族史。如果说达乌德的“朝圣之路”尚且还带有一丝绝境求生的不得已,多蒂的身份认同则增添了几分自我建构的主动性。
尽管这三部作品从不同的叙事视角记录了移民在英国的经历,探讨了迁移到一个新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对人物身份带来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此时的古尔纳还未能跳出个体视角和局部剖解的框架。直到1994年《天堂》的出版,才标志着他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自我突破。这部同时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和惠特贝瑞图书奖的作品,通过男孩尤素夫的眼睛看尽了部落争斗不断、迷信盛行、疾病肆虐、奴隶贸易猖獗的非洲。比起前作,《天堂》拥有了更广阔、宏观的视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部庞大的非洲编年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副教授张峰认为,这种由现实向历史扩展的创作谱系,似乎是具有相似背景的作家在创作上的一种共性。作家克莱尔·钱伯斯则在《英国 *** **——当代知名作家访谈录》一书中,指出了从《天堂》开始古尔纳创作的另一显著转变:“在写作《离别的记忆》的时候,他尝试写出主角对于离开的渴望,而如今他想写作的内容却是主人公虽身在国内仍有一种甩不掉的孤独感。”
尽管诺奖在授予古尔纳的颁奖词中,着重强调了其写作对殖民主义的探索和难民命运的关切,但或许“孤独”更能概括他文字中那个萦绕不散的核心。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在评述中所写:“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是其身份认同。他笔下流动的人物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
2011年出版的《最后的礼物》是古尔纳的第八部**,同样延续着移民主题。不同的是,它聚焦于移民经历对移民自己及其后代的无尽影响。而在第九部**《碎石之心》中,主人公在母亲去世后再一次面临着那个艰难的选择——应当留在桑给巴尔,还是回到伦敦?在一次采访中,古尔纳说:“在危机时刻,人们会一次又一次重返 ‘我应当在哪里’的问题。”
在张峰看来,这恰恰是后殖民文学的意义所在。“后殖民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思想的终结,因为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宗主国或殖民文化的终结,它在殖民地上已经扎根了,而且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都会影响殖民地人的方方面面。后殖民文学与殖民文学不是截然分离的两个阶段,而更多意味着一种延续,以及这些来自殖民地的人和来自殖民地又迁移到宗主国的人对于殖民意识形态的不断反思,包括对独立之后的后殖民身份的不断考量。”在一篇题为《An Idea of the Past》的文章中,古尔纳也对殖民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做出过他的阐释:“对非洲人来说,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影响是当代事件,重点正在于其当代性,殖民主义构成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过去,也形成了它们的当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接受“后殖民主义作家”这样一个标签。他明确表示过:“我不会使用这些词,我不会让我自己戴上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标签。事实上,我不确定除了我的名字我还会怎么称呼自己。”与此同时,古尔纳对于后殖民写作也保持着清醒的警惕,他认为将矛头单单对向曾经的殖民帝国、将所有社会症结归结为殖民统治的毒害是一个陷阱,非洲内部民族和部落分裂所带来的危害一样可怕。并且“对后殖民主义作家来说,危险似乎在于,这可能会在一个欧洲外来者疏远与孤立的生活中已经或将要产生作用。如此,作家很可能成为一个愤愤不平的移民,嘲笑留下的人,并得到那些出版商与读者的欢呼——他们对殖民地人民仍存有隐秘敌意,且乐于奖励赞扬对非欧洲世界的任何苛责。”
与中国的奇妙连接
去年9月,古尔纳推出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来世》,以1907年反抗德国殖民者的起义为开场,展示了几代人历经德意志帝国统治与英国殖民,努力维持着他们位于坦桑尼亚大陆一个沿海小镇上的家庭与社会。许多评论将之视为《天堂》的续作。
然而最重要的始终是古尔纳想要表达的思索。《卫报》的一篇书评说,“大部分有关欧洲在非洲殖民历史的讨论都将德国排除在外,但实际上建立于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殖民过今天的纳米比亚、喀麦隆、多哥、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并最终夺取了卢旺达和布隆迪,其殖民统治是残酷的。古尔纳在这本书中思考了殖民主义和战争的代际影响,并促使我们思考在如此巨大的毁灭之后还剩下什么。”这的确是古尔纳所在意的。
可以想见的是,在诺奖的加持下,这本《来世》必然要比古尔纳的几部前作更快更广地传递到读者手中。对于尚无译本可读的中国读者来说,与古尔纳的相遇相信也不会太远。一个有趣的例子或许可资证明: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卢敏,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的成员,负责东部非洲研究的她从2019年起就开始研究古尔纳。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庆节前自己刚好分给学生一个任务,每人读一本古尔纳的**然后写出作品简介,结果诺奖的新闻一出,许多媒体便找到她索求资料,于是学生们这几天都在拼命赶稿。
同时,在卢敏的研究中,她还发现了古尔纳与中国的一个奇妙连接:“他几乎每一本书里都会提到中国或者华裔,也会提到中国建铁路,还会提到中国的一些产品。他在《多蒂》里面反复讲到一个中国公主,就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巴杜拉公主。”
我们尚且不知这种连接在古尔纳的内心从何而来又意在何为,只晓得这份缘分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种下了。据古尔纳在BBC的一档历史系列节目中回忆,自己年轻时在桑给巴尔岛上发现过几片中国瓷器碎片:“直到当你参观博物馆,或者当你听到那些关于中国舰队远赴非洲探险的伟大故事时,这些小物件才变得有价值,成为某个重要事物的象征,或者说是一种联系。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物件本身,看到它的整体性、它的重量、它的美。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像中国这样遥远的文化,在远隔几个世纪之后出现在此。”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8期
二:现代真实灵异事件簿成了精的黄鼠狼
我今天要讲的的确是一个惊悚的“鬼故事”,不过非常的离奇,也可以说是一个**版“鬼故事”。
故事发生在吉林省榆树市的一个农村,正举办着一场农村隆重的葬礼,吹鼓手们使劲吹着揪心的唢呐曲儿,雇佣来“哭包”的人悲痛地哭着,虽然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死者,他们只是为了烘托悲伤的气氛。
死者停在灵堂上,穿着一身寿衣,这是死者的大哥受父亲的嘱托,特意去镇上定做的,看起来非常合身。死者已经经过美容师美容,脸色惨白,顶着那头标志性的黄头发,不过已经没有人上前来仔细看她的容貌了。屯子里的人都来张家致哀,然后就在张家的院子里大吃一通,再打包带走一些吃食回家。

尸体已经停了两天,按照当地的习俗,明天早上就是出殡的日子。死的是张老汉家的四女儿,她是寒冬腊月死在了野地里,是冻死的,没有别人加害的痕迹。
警察是挨个村子来通知认尸体的,张丽的家人这才知道离家出走的张丽可能出了事,当家人跟着警察去认领尸体的时候,尸体已经被冻硬,脸上已经呈现了紫色,面目实在是看不太清,不过那一头黄发却辨识度很高,所以尸体被家人拉了回来。父亲为了弥补女儿的早亡,决定风光大葬四女儿,这才有了前边的一幕。
第二天一早重头戏来了,张丽出殡了,她的棺材被浩浩荡荡的人簇拥着,埋葬在了村头的墓地里,而且在坟头立了墓碑,由于是农村,所以也没有去火葬,就这样连着棺材土葬了。
事情看来可以结束了,哪知这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七天之后,村里人的谣言像瘟疫一般迅速传播开来,说有人看见张丽在村子里游逛,难道七天上旺这个传说显灵了?张丽的鬼魂真的回家来了?一时间屯子里人心惶惶,甚至白天都把门锁起来。
头七当天的当晚,张丽的小妹夫和别人喝了些酒,路过张丽的坟头的时候,黑暗中看见一个人蹲在墓碑前,正在啃食供品,而且坟上还被掏出了一个大洞,他越看那个人越像他死去的四姐张丽,他吓得魂儿都出来了,也没敢吱声,一溜烟就跑回了张家。
到了张家就和张丽的大哥张军说了这事,以大哥为首的一家人,都觉得他是在说酒话,一定是喝多了,想念四姐产生的幻觉!妹夫有口难辨,只好作罢。
随后的几天屯子里传得越来越凶,张家人也不由怀疑了起来。尤其是大哥张军,走在路上的时候,总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不过没有亲眼见到,他也就没有去和人辩解。
直到有天晚上,正在自家炕头躺着的张军,忽然被院子里传出的“哐当”一声吓了一跳,媳妇才去了老妈家,院子里不是进贼了吧?想着,他抓起手电就冲出了屋子,院子里真闪过一条人影,张军用手电一晃,应该是个女人,一头黄发,张军马上就头皮发麻,这明明就是四妹张丽啊!不过那人没有停留,飞快地跑远了,张军也没敢去追。
转过天,已经相信了八九分的张军,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找了屯子里几个胆子大的,白天来到了坟地,真的看到一个人在吃供品,那人正是张丽!张军战战兢兢地把张丽接回了家里,张丽浑身**秽不堪,没了人形,家里人给她换洗了一番,第二天就带她上了医院,医院的检查显示张丽的身体非常健康,只不过这精神嘛,有点麻烦。 家里人也知道她精神上的毛病,直接就把张丽送进了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
张丽究竟是怎么患上精神疾病的呢?这要从张丽的没结婚时说起。当时张丽自由恋爱和丈夫徐大明结婚了,在当时农村自由恋爱可是个新奇的事儿,这也间接说明了张家对张丽的疼爱,尊重她的选择。婚后丈夫就进城做起了生意,然后他们的孩子出生,逐渐长大。到了后来,风言风语的传来,说徐大明在城里有了人,在这件事上张丽还是相信丈夫的,不过也藏了一个心眼,有天自己谁也没有告诉就到了城里,把丈夫和小三堵个正着,悲愤的张丽决定和丈夫离婚。离婚手续很快下来了,孩子跟了父亲,而后徐大明迅速地又组建了家庭,张丽却孤家寡人,她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打击,终于精神上被压垮,她疯了。
据张丽的大嫂说,张丽犯病的时候,有十足的暴力倾向,打人,不论身边有什么东西,**起来就打人,有棍子拿棍子,有菜刀就拿菜刀,往人身上招呼。曾经把自己的老母亲胳膊打折,头上还砍开了花,对自己家人况且如此,更不用说屯子里其他人了,所以屯子里的人都躲着张丽走。这也难怪说张丽没死的时候,大家都噤若寒蝉的。
这下人活了过来,那又有三个疑问摆在了大哥张军的面前。
一是如果张丽没死,那么那个已经入殓的尸体是谁的?张大哥承认当初去看这尸体的时候,姊妹几个只是大致辨认了尸体,觉得精神不正常的人极有可能冻死在野外,大嫂也表示谁都不敢真正的去仔细辨认尸体,只是觉得那一头黄发肯定是张丽无疑,那么下一步就希望真正尸体的家人前来认领这尸体。
二是张丽第一次出走到葬礼举行这段时间,她去了哪里?她的去向也成了疑问,但张丽现在自己无法描述出经过来。
三是这坟头上的洞是怎么来的,并没有人真的起死还生。屯子里的老人也就此给出 答案,一定是黄鼠狼打的洞,把坟墓里当成了自己的窝,在里边居住,事情终于水落石出,我们也祝福张丽早日康复。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可以溯源的鬼故事,一个阴差阳错的故事。
我是一念,欢迎
三:中国真实灵异事件簿有声**灵异事件真实(作者:炽焰)
中国灵异事件备忘录(作者:夜半微风老鬼)
现代真实灵异事件薄(作者:痛快)
灵异事件录(作者:冰叹雨)
真实灵异事件:诡案组(作者:求无欲)
灵异事件簿(作者:冥海)
灵异事件(作者:我们踢球吧)
现代真实灵异事件簿(作者:)
上海灵异事件薄(作者:季顺p)
灵异屋:诡异事件!(作者:墨兮染流年)
白夜灵异事件簿(作者:风魂)
直击灵异事件(作者:sealzheng)
Eskey灵异事件簿(作者:Eskey)
重庆灵异事件薄(作者:刘中轩)
都市灵异事件辑(作者:情无恋ㄤ心)
成理灵异事件(作者:MY铭扬天下)
校园灵异事件集(作者:逸儿)
《网游之灵异事件(作者:起点零零发)
网游之灵异事件(作者:起点零零发)
《鬼宅灵异事件(作者:伍拾元)
这个符合你的口味?我爱读电子书找来的
标签: 古尔纳 张丽
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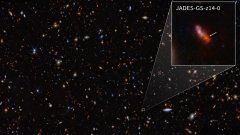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郭爽男友现状,郭爽男友现状照片 神秘事件10人阅读
郭爽男友现状,郭爽男友现状照片 神秘事件10人阅读 -

-

-

-

-
 青城山僵尸是真的吗? 神秘事件10人阅读
青城山僵尸是真的吗? 神秘事件10人阅读 -
 有趣但无味(有趣无味的反义词) 神秘事件0人阅读
有趣但无味(有趣无味的反义词) 神秘事件0人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