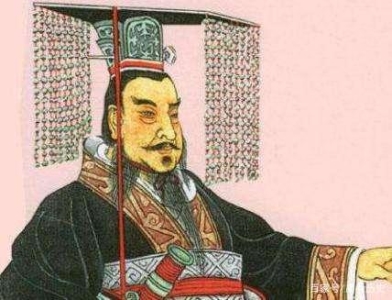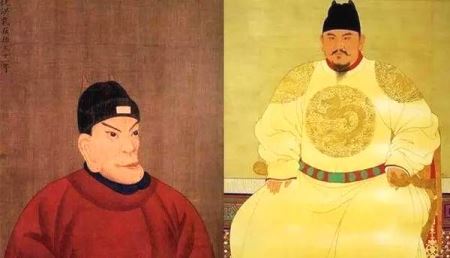正德帝王朱厚照的七大极品嗜好:花花公子朱厚照
却又不知从哪里下笔。

主要是这位叫的帝王让我们没法用一个完整的结论去评价他。
他到底是一个顽皮的孩子?还是一个愤青?还是一个有为的“将军”?因为按传统的道德去看他,那真是叛逆到极点了。
他十四岁登基,三十一岁死亡。
期间的历史,可以用荒诞不经来形容。
往往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在他身上。
下面就让我们遵循历史的脚步,先看看他的所作作为吧。
时间到了公元1505年,勤政,英明的因伤寒加上太医误诊,错服药物,导致病重,最终鼻血不止逝世。
由于的后宫只有只有张皇后一人,生下二子三女,其中二子朱厚炜早年夭折。
这也为孝宗绝后埋下了伏笔,造成了明代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大礼仪之争。
可见,封建社会多子也不是一无是处啊?皇长女太康公主也因病去世,所以孝宗只剩下朱厚照这一个儿子,对他当然是万般呵护,所以父子二人情感很深。
孝宗想要的天伦之乐,终于实现了。
翻看明代的帝王历史父子相善,恩爱有佳的。
也只此一例。
在朱厚照两岁时就被立为太子。
史书记载小时候的朱厚照那也是聪明伶俐,一幅英明果敢的形象。
可是面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成长环境。
想想我们现在的独生子女,似乎就可以初窥到他后来的所做所为的原因。
1506年,正德继位。
是年14岁。
第一爱好,体育舞蹈。
这位哥们在东宫时候就宠以刘瑾为首的“八虎”。
大搞百戏表演,一时间的东宫,抖空竹的,溜冰的,相扑的,打渔鼓的,拉皮影的,弹词的,吐火的,玩杂技的等等。
。
一时间,各界能人纷至沓来,好不热闹。
。
。
第二爱好:喜欢动物。
武宗开创了封建帝王豢养动物的最鼎盛的时期。
皇家出资设立“豹房”,一时间,老虎,大象,狮子,鹁鸽,长颈鹿,鹰隼,等等简直是国家的国立动物园了。
一次皇帝突发奇想,要将老虎训练成听话的狗,结果不但没有成功,朱厚照本人也差一点被所养的老虎吃掉,所幸被随侍侍卫江彬所救。
一虎易除,一虎又出,这个江彬后来成了后来正德后期的大奸臣之一。
为了驯养这些动物,内廷出资颇多。
仅随驾侍养的那头豹子,就有240人伺候着。
从中可见豹房的花费。
。
。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曾研究过建立的豹房,对此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
涉及到对武宗的评价(如武宗不是庸君,很有才华),对豹房性质的探讨(如豹房不是淫乐场所,而是武宗治理朝政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总部)。
1994年3月《北京文物报》上《豹房非豹房之新探讨》一文还提出“豹房”原字音出阿拉伯语“巴欧坊Ba—Fen”之谐音转成“豹房”,其意译为“技艺学术研究中心”。
是我们的文人需要思考了,还是我们需要思考。
也许我们都需要思考。
是有人篡改了历史,还是需要重新认识历史?影视剧中的朱厚照 第三爱好:喜欢表演。
可能什么都想尝试下,朱厚照又在后宫和大家演起了一出古代电影。
。
在皇宫建了个古代“好莱坞”。
电影的主演,制片,发行,观众,导演就是这位皇上自己。
他身穿古人服饰扮成富商。
内侍宫女扮成商人杂役,广置货物。
一时间宫内,商铺林立,酒旗飘扬。
只见一位公子,翩翩而来。
与众商家谈价钱,谈商机。
在这不经意的一买一卖中,赚个盆丰钵满。
累了住店,渴了饮酒。
心情好时,还不忘逛逛怡红院。
第四爱好:喜欢军旅。
朱厚照小时候学习过鞑靼语。
并且了解回族风俗。
正德烧造了很多带有回文的瓷器。
又给自己取名为沙吉敖烂;学西番麻僧教,则自名为太宝法王领占班丹。
他给自己改名字叫“寿”后,还专门命所司造了个御马太监天字一号牙牌。
时间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蒙古鞑靼部在小王子的带领下南下。
一时间朝野震惊。
朱厚照本来可以居中帷幄,调兵遣将。
谁知他做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决定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是决定御驾亲征。

由于他的太爷爷正统皇帝,曾有北征被俘的经历在前。
所以朝中的反对声浪很高。
正德帝,乾纲独断。
亲率几万兵士,同吃同住,明军士气大振,终于取得了一场胜利。
正德御驾亲征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以伤亡600多名士兵的代价打死了16名鞑靼军人。
历史上杀伐数字的统计夸大早已有之,但这次却出奇的精确到人。
且对胜利少有称颂。
做为文官制度中的一分子——史官。
在记录的同时仍不忘揶揄一下。
但是恰从中让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和官僚体系出现的问题!!!不管皇帝的功绩是否被抹杀,亲征的后果是终正德一朝,蒙古再也没有南下。
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沸腾,不畏牺牲的英明君主形象。
可是下来的事情就朝着匪夷所思的方向发展。
加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并改名朱寿。
开着玩笑自己加封自己过了一会将军瘾。
仿佛是觉得挺好玩的。
1518年秋,又命内阁的大学士起草诏书,再次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厚照(字寿)”“出师西北巡视边靖”。
这一回,还没到目的地,正德就忙着下旨封自己做“镇国公”,“岁克俸米五千石”到了西北,在四处搜寻敌寇以求一战的无聊日子,正德再一次下旨封自己为太师,位居内阁大学士之首。
如此一来,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具武功的王公和最具权威的文官。
由于朝政的荒废,宁王朱宸濠妄图效仿,趁武宗荒于政事,秘密准备叛乱,并于正德十四年扯旗造反。
武宗皇帝并未因此而着急,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南巡的机会,于是他又打起了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可谁知行到半路御使已经平定了叛乱。
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降低武宗的兴致,他又一手导演了一幕闹剧,他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由自己亲自在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宫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
1519年,正德皇帝又准备命令自己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巡幸南方各省。
一时间朝廷上闹得乱哄哄的。
官员们再也忍不住了。
纷纷午门“跪谏”,皇帝劝说无果。
一筹莫展的时候。
在豹房救过皇上性命的“打虎英雄”江彬出场了,此君不但会打老虎,打起大臣来那也是不含糊的。
在正德的授意下,将跪劝不去的146名官员每人赏梃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伤杖毙(有的是被家人领回家后伤发而亡)。
有个大臣当着他小儿子的面被打死。
此事一发生,全体内阁大学士引咎辞职但不被批准。
朱厚照是不是因此被感动了。
不得不得而知,南方之行也因这场风波延宕了几个月之久。
第五爱好:喜欢旅游。
与那些养在深宫,几乎一辈子不出宫的皇帝比起来。
正德皇帝真是个另类。
登基后,几乎没有消停过。
射猎在东宫就玩腻了。
喜欢到处跑。
甚至为此送命也痴心不该。
要在现在,怎么看那也是一个坚定驴族啊。
可惜错生在帝王家啊。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八月,朱厚照突然“急装微服,出幸昌平。
”朝中大臣得知朱厚照微服出行的消息,惊诧异常。
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人急忙出朝驾了轻车,地追赶,一直追到沙河,才追上朱厚照,苦苦谏阻,请他回宫。
朱厚照不听,非要出居庸关不可。
幸好把守居庸关的巡关御史张钦坚持原则,紧闭城门,仗剑坐关门下,号令关中:“有言开关者斩!”硬是不放朱厚照出去。
朱厚照大怒,传旨捉拿张钦。
但这时京中各官的奏疏像雪片般飞来。
朱厚照读都读不过来,越觉躁急得很。
江彬见群臣汹汹,连忙上前劝道:“内外各官,纷纷奏阻,反闹得不成样子,请圣上暂时涵容,以后再作计较。
”朱厚照这才悻悻还朝。
但朱厚照并没有死心,隔了几天,下旨派张钦出巡白羊口,换了自己的亲信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守居庸关,随即与江彬换了服装,在夜间混出德胜门,扬鞭出关,到了宣府“镇国将军府第”的行宫。
在江彬的引导下,朱厚照在半夜随意闯入宣府高门大户,迫令妇女出陪。
朱厚照游完宣府后,又跑到大同等地游玩。
正德皇帝的南巡于1519年秋得以实现,江南的美景和气候给喜欢纵情游乐的正德添加了兴奋剂,正德只要兴之所至,可以说无所不为,要命的是在一叶扁舟去撒网捕鱼节目中,正德的小船翻了。
落入水中的正德虽然很快被救了上来,但从此龙体染恙,一直不见康复,他1520年底回到北京后,1521年初就在他的豹房殡天了。
享年不满30岁。
第六爱好:爱好。
皇帝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
”粉黛六宫,佳丽三千。
佳丽如云啊!!!可是仍不能满足这个年轻人。
日久觉得无趣,就在后宫模仿开了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当然主顾只有一人,朱厚照挨家进去听曲、淫乐。
后来觉得不过瘾就外出坊间,留宿歌楼妓院。
时间不长又觉得没意思。
就设立豹房。
武宗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然而他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而是将喜欢的女人都放到了豹房和宣府的镇国府。

武宗远离后宫而钟情豹房,是因为与夏皇后感情不和,还是有其他原因,是一个无法考释的谜。
豹房之内,美女如云,武宗过着恣意妄为的淫乱生活,极大地满足了他的感官享受。
这里充斥着教坊司的女乐、高丽美女、西域舞女、扬州少女,乃至于妓女、寡妇等各色女子。
豹房之内到底有多少女子,恐怕连武宗自己都不清楚。
那些一时无法召幸的女子,就被安排在浣衣局寄养,以备武宗不时宣召。
这里既包括内臣进献的,也有武宗自己游幸各地带回来的,人数之多,难以想像,据说经常有因饥饿、疾病死亡者。
宣府是武宗另一个淫乐窝。
他刚到宣府之时,在这个远离国都的军镇,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
每到夜晚,武宗带上一队亲兵,在空荡的街道上闲逛。
看见高墙大院的富庶之家,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然后入内强索妇女,弄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那些富有之家纷纷重贿江彬,希冀能够免除祸患。
南下平叛时,路过山东临清,皇帝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一个月。
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
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刘娘娘。
武宗对刘良女非常好,凡是豹房中有谁偶尔犯了小错,只要刘良女在武宗面前替他求情,武宗就不会追究。
此次南巡,武宗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
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
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因无信物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个月。
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关于武宗与刘良女相识的经过,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明实录》中记载刘良女是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
武宗游幸山西时,派人到太原索要女乐,得到了刘良女。
武宗喜她色艺俱佳,就从榆林带回了豹房。
《稗说》则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
刘良女是大同代王府上有名的歌姬,武宗曾假扮低级军官出入于王府的教坊,因而得以认识刘氏。
当时武宗在这样的风月场所中并不太引人注意,别人还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军官而已,但是刘氏慧眼识珠,认定他不是个平常人,就对他另眼相看。
武宗记住了这个刘氏,后来派人将其接到北京。
这就成了后来著名戏曲《游龙戏凤》的故事框架,只不过刘氏变成了李凤姐。
武宗下江南时,刘氏一直陪伴在身旁,多次一同出现在臣民面前。
武宗在南京赏赐寺庙幡幢上都要写上自己和刘氏的名字,刘氏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宠爱的女人。
第七爱好:爱收养子。
武宗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100余个义子,甚至在正德七年一次就将127人改赐,真是旷古未闻。
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
钱宁,本不,因幼时被卖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
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为尚武的武宗所喜欢。
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
据说武宗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地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
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
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但他毫无惧意,拔之再战。
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武宗意,遂被留在身边。
可惜这些儿子成为志世能臣的一个也没有。
徒留了些恶名给武宗抹黑。
历史是很有趣的,收了那么多养子,而真正的皇家骨肉却一个也没有。
14岁登基,30岁死,期间近17年。
夜夜笙歌,多少却没有子嗣,这是他心头无法抚平的伤痛,为此他甚至导演了迎娶孕妇的闹剧。
正德十一年,赋闲在家的马昂为求得复职升官的机会,结交武宗身边的红人江彬。
江彬极力在武宗面前赞扬马昂妹妹美若天仙,又娴熟骑射,能歌善舞。
武宗一见,果然异常欢喜,不顾她已有身孕,将其从宣府带回豹房,并给马昂升官晋职。
其实武宗宠幸,却另有一番打算。
因为在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后,他就想借此瞒天过海。
朝臣听到了一些风声,又见马昂超授右都督,知道了传闻属实,就纷纷上疏要武宗驱逐马氏,以绝后患。
也不知道是奏疏中“进孕女”这样的典故让武宗幡然醒悟,还是见到事情已经泄露,武宗倒是逐渐疏远了马氏,也就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也许朱厚照收那么多养子的原因,正是没有子嗣带来的一种心理安慰吧。
明武宗,朱厚照,出生于公元1491年,公元1505年即位,到1521年病死,享年31岁,在位17年,年号正德。
谥号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康陵。
皇后。
无子女。
到最后,浩瀚的历史中,介绍这个好玩的大男孩就这么多。
不管好也罢,坏也罢。
都得落幕。
就留作后人评说吧。
。
。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