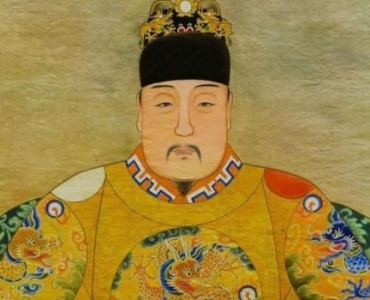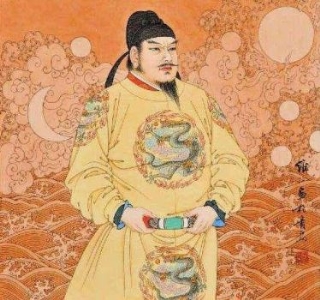中国古时候史上一个女子的抗争引发的一场法律变革
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律修订和变革,往往是伴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和朝代更替进行的,因为一个女子的抗争从而引发一场法律的变革,却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

在时代,这样的事情还真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引发这场变革的女子叫做缇萦,她是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的第五个女儿。
一般认为,这场变革是汉文帝的宅心仁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因为缇萦的抗争,如果缇萦随波逐流于那个时代的一般行事方式,这场变革有可能不会发生,或者至少要晚一些发生。
文帝十三年(前167),齐国的太仓令(管粮库的官)淳于意犯了罪被押送到京城长安拘禁起来。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
临行时他骂女儿们说:“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用处了。
”他的小女儿缇萦(音:tiying)伤心地哭了,就跟随父亲来到长安。
她向朝廷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因触犯法律而犯罪,应当受刑。
我哀伤的是,受了死刑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受了肉刑的人肢体断了不能再接起来,虽想走改过自新之路,也没有办法了。
我愿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来抵父亲的应该受刑之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
”这封上书还真的到了汉文帝那儿,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下诏说:“时期政治清明,只要在有罪的人帽子上画上一个记号,民众就不犯法了。
如今法令中有刺面、割鼻、断足三种肉刑,可是犯法的事情仍然不能禁止,这是因为我道德不厚教化不明所致。
现在人犯了过错,还没有施以教育就加给刑罚,那么有人想也没有机会了。
施用刑罚以致割断犯人的肢体,刻伤犯人的肌肤,终身不能长好,多么令人痛苦而又不合道德呀!作为国家的最高父母,这样做,难道合乎天下父母之心吗?于是下诏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代替。
并依照犯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只要他们不逃亡,期满免罪。
同时命令有关人员制定出相关法令。
这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有期”徒刑吧!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犯了罪,要么处死,要么肉刑,剩下的就是徒役,也就是奴隶,根本就没有“期满免罪”之说。

根据汉文帝的这个诏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提出了具体建议条文:应该判处髡(音kun,拔光头发)刑的,男的改罚城旦(修城墙),女的改罚舂米;应该判处黥(音qing,面部刺字)髡刑的,改为剃发、颈带铁链,男的城旦,女的舂米;应判处劓(音yi)刑的,改为鞭笞三百;应判处刖(yue)刑的,砍断左脚改为鞭笞三百;应砍断右脚以及杀人自首、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已经顶罪而又犯了鞭笞罪的一律公开斩首。
已经判为城旦、舂米的,服刑到一定年限,就可免罪。
文帝同意了这些条文。
这些法律条文的改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古人认为“人之发肤受之父母”,头发是终生不能剃掉的,拔掉头发、脸上刺字、割掉鼻子,他不再是一个社会上的正常人,表明他都是一个“罪犯”。
当一个人被判处这样的刑罚,丧失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资格,他还能继续娶妻生子存在于社会吗?封建社会是农业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父子传承,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了儿子,一旦犯了法被判处这样的刑罚,谁又会让女儿嫁给这样的家庭?这就是缇萦和汉文帝都提到的“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的原因。
改为修城墙、舂米等劳役活,到了期满,这个人回到了家里,也就是正常的回归了社会。
砍脚的那种刖刑更不用说,他不仅不能作为正常人存在于社会,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还会成为这个家庭的重大负担。
可见,这样的法律条文的改变,其意义是革命性的,称之为变革毫不为过。
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缇萦的抗争,才导致了这样一场重大的法律变革。
那么,缇萦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抗争呢? 和世俗观念抗争 父系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缇萦的父亲淳于意也不两样,出了问题,他想到的是自己没有儿子。
因为没有儿子,他不拿家当家,到处交游。
因为他医术高明,对一些不肯治疗,因此被病家怨恨并告发。
这也可以看做是没有儿子的原因,假如他有儿子,告发他的人有可能害怕结怨仇家而费一番思量。
缇萦是一个弱女子,听到父亲的话她也会哭,但她并没有沉默,而是选择了奋起抗争。
她跟随父亲到了首都长安,并上书。
从齐国到长安,路途万里,其艰辛可想而知。
如果说这个可以通过毅力坚持的话,上书皇帝则更是需要超常的勇气和智慧,缇萦是一个小官的孩子,是一个没有爵位、没有继承资格的女子,她敢于上书皇帝,没有一种抗争精神是做不到的。
和法律条文中的非人性的一面抗争 缇萦的上书,抓住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人性中的悔恶向善。

一个人可能一时会有罪恶的念头,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对自己的不法行为后悔,真正死不悔改的人少之又少。
肉刑这种侮辱性的刑罚恰恰是堵住了人们悔改之路。
缇萦大胆地指出了这种刑罚的弊端,提出了“想走改过自新之路”这个人性中悔过向善的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她不是仅仅提出“愿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为父亲顶罪,而是先指出肉刑的非人性,然后说让父亲能够“改过自新”!难怪这样的抗争能都得到汉文帝的认可!如果不是缇萦和法律条文的抗争,而她仅仅选择替父亲顶罪,汉文帝能够引起自责并作出废除肉刑的决定吗? 和法律传统抗争 封建社会的观念,父业子承,相对应的是“父债子还”。
如果犯的不是之罪,按照汉代的法律传统,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抵罪的,比如说以钱抵罪。
如果淳于意有儿子,他可以选择以自身或其他方法抵顶其父之罪,但是淳于意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他没有了指望,他只有哀叹:“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用处了”。
可是缇萦不认可,她主动提出以自己没入官府做奴婢为条件,换取父亲的自由。
所以说她是在和法律传统抗争。
女子被没入官府为奴婢,一般情况是自身犯罪或者是受父、夫牵连,主动提出来以身为父亲抵罪,不是当时的社会传统,也就不是当时的法律传统,缇萦这样做了,所以说是抗争。
当然,缇萦的抗争能够引发一场法律的变革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汉代社会的开明、汉文帝宅心仁厚等等。
诸侯国的太仓令算不上大官,一个小小官吏的女儿为何能够给皇帝上书?而这样一个小女子的上书又为什么能够交到皇帝手上?想想能够“称制”当上实际上的皇帝,的母亲嫁了人生了孩子还能再嫁给皇帝,就可以知道汉代对女子的宽容,它既超过了前人,也为后世整个封建社会所不及。
缇萦的上书,隐含着对法律条文的指责,汉文帝看到了缇萦的上书,没有生气发怒,这不是一般皇帝能够做到的。
汉文帝不但做到了,还从自身寻找原因,并做出了检讨和改变,当然是这场变革的主角。
不管怎么说,这场法律的变革是由缇萦上书救父引起,她的孝心、智慧和敢于抗争的勇气令人敬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