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两年里,独立设计或引进生产保安用具的大小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保安队伍也从无到有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分别于公安的准警察组织。现在,人们走进任何一家储蓄所或银行分理处,都会发现一名以上穿深色制服、腰佩手枪、手持警棍的保安人员坐在座位上,警惕地打量着每一个推门而入的陌生人。自然,犯罪与保安行为是轮番升级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进入90年代中期,银行运钞车代替银行建筑成为犯罪分子袭击的重点。
1996年2月8日,也是在春节前夕,北京市安惠里甘水桥工商银行分理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刚刚在保安人员的护卫下把“略有沉重”的密码箱装进运款车,分理处南侧位置停着的一辆藏蓝色“大宇”轿车里中冲出一名端枪的蒙面人,将正准备上车的保安员打倒在地,又向车内其他人射击,抢走两个装有巨款的密码箱驱车逃走。同年6月3日晨,一辆运钞车从北京海淀知春里银行开出,驶离50米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去路,车内冲出的蒙面人手持冲锋枪,逼住运钞车司机取得钥匙,将后备箱打开抢走两只“铝合金提款箱”。而在8月27日上午,同一罪犯伙同另一名歹徒在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支行附近截住运钞车时,遇到顽强的抵抗。罪犯在打倒4人后击碎运钞车后备箱内的玻璃,却发现“即打不开款箱,也搬不动款箱”,只好“仓惶逃窜”。从这起系列大案中,可以见到抢劫与防范手段不断进展的古代过程。小金鹤储蓄所当天的库存现金2万多元。两名罪犯徒步逃离现场,沿途有多人目击。紧挨储蓄所的一家食杂店老板崔XX提供情况说,当日下午15时47分左右,他出去倒灰,看见从储蓄所跑过来一高一矮两个青年人,“小个1.60米左右,穿挺瘦的衣服,什么式样没看准。”戴什么帽子没注意,也没看见手里拿着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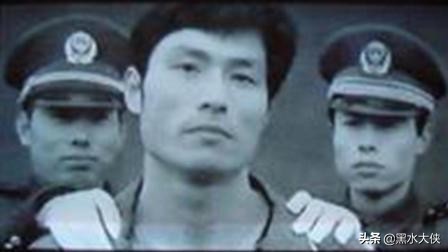
侦察员问他再见着这两个人是否能辨认出来,他说不能,走对面也认不出来。在他家附近无人议论此事。南山区二建工作的刘XX当日从杀猪厂附近路过,看见一前一后两名罪犯与他相反的方向跑去。其中小个子男人二十五六岁样子,挟黑色人造革拎包,穿深色上衣、浅色裤子,圆脸,脸较白,身高1.65米左右。大个子男人二十三四岁,穿普通半新灰上衣、蓝色旧裤,脸较白,身高1.73米左右。以前未见过这两个人。当侦察员向他出示犯罪分子模拟画像时,他认为有点像大个子男人,但脸没有画的胖,眼睛也没有那么大。他看见两人往向阳区化工厂左边的胡同跑走。如再见到“不敢说能认识”。住向阳区十八委的一名14岁的小学生吴X那天从院里提桶出门倒水,看见那两个人从化工厂那条道往下跑,跑进向阳区五金商店旁边的胡同里。后面的人手里拿一把黑色手枪,边跑边往衣服里藏。前面的小个子穿灰色上衣,1.60米左右,手拿一只黑色的皮包。嘴里说着“快跑!”后面拿枪的大个子有1.70米左右,往衣服里插枪时能看到枪的后半截。侦察员把自己的“五四式”手枪展示给这名学生看,该学生说这枪和那两人带的枪是一样的。当日下午15时30分以后,住向阳区十八委的两个小学生在门口玩,也看见了那两个人。赵XX说他看见的高个子男人穿黑皮夹克,脖领上带毛。矮个子男人穿呢?子上衣,敞着怀,跑跑又停住,并把一支手枪揣在怀里,没插好,枪把掉了出来,又急忙往回塞了一下,两人就跑远了。12岁的杨XX认为他看见的高个比侦察员(1.73)高点,右手好像包着布,手里拿着枪,把枪插到怀里。后面的矮个比他矮一头,穿深灰色上衣,两个都没戴帽子。他们从杨XX家对面的胡同里跑下来,跑到胡同口站下,前面的高个问杨XX和曾XX两个孩子前面是不是死胡同,曾XX说是,后面的矮个就招呼前面的高个,指着另一条胡同说:“从这跑!”因为看见了枪,两个孩子好奇地跟过去,在那条胡同口看见两人向右拐了下去,穿运动服的人回头望了一眼,吓得两个孩子都跑回来。

14岁的曾XX认为他看见的高个穿灰衣服,1.70米以上身高,戴前进帽。那天矿务局总医院服务公司的王XX下班回家,在家门口看见两个人从对面跑来,小个子穿深色中山服,比大个子年长二三岁、圆脸。大个子好像穿半截大衣、深色,左胳膊夹个黑兜子,瓜子脸,脸色较黑,身材较瘦。两人跑远后,有个胖子走过来对王XX说,刚才那两人可能是“拎包”的,王XX说是,就回家了。曾与歹徒抗争的小金鹤储蓄所所长王人伟描述说:持枪罪犯身高1.70-1.72米,年龄20岁左右,体态中等,长瓜子脸,中等眼睛,左眼有点斜,是格棱眼,头戴黄色毡绒帽,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似乎是圆领”,裤子没看清。此人说话为本地口音。另一名罪犯年龄比持枪罪犯稍大,也比持枪罪犯稍高一些,25岁左右,其他印象不深。两名女营业员则坚持认为站窗前的歹徒比持枪歹徒矮一些、胖一些,圆脸。储蓄所的3个人都说,如果再见到歹徒能认出来。上述证词描绘了两名罪犯从抢劫到逃离的一长段过程,但大家对他们体貌、穿着、年龄上的追忆互相多有矛盾之处。归纳起来,警方倾向于肯定:(1)两名罪犯都是本地人。(2)高个子罪犯身高1.71-1.72米,体型适中,瓜子脸,左眼下斜,上身穿半截呢?大衣,持“五四式”手枪。(3)矮个子罪犯身高1.68-1.70米,稍胖,圆脸,皮肤较白,逃跑时拿着拎包。这样看来,两人与“1.28”破案指挥部《通告》中明确提到的两名罪犯确有相似之处。曾参加“1.25”案件破案工作的王春林介绍说“从作案经验和作案手段来看,这两个人显然9不能与‘1.28’案犯相比。他们没有交通工具,逃跑时靠两条腿,沿途被多人注意,可以说很危险,即使抢到钱,怎么摆脱追赶也是个问题。

他们本以为有枪就能抢到钱,没料到遇到对方的反抗,一下子就慌了手脚,逃走时也不像‘1.28’案犯那样预先规定了逃跑路线,有点乱闯,差点儿走进死胡同。但我们当时分析,这两个人还是有脑子,事先的策划不一般。”闫自忠点点头,评道:“策划上的确有路数。第一,去抢钱的时间刚好是储蓄所结账的时间,也是一天里现金最多、顾客最少的时间,事先肯定作过详细调查;第二,全城储蓄所不少,专门选择离公安局最近的地方抢,不会是偶然的,大概认为那里的戒备最松懈。这后一条在当时已经算是高智能犯罪了。案子没破是什么真相?”李洪杰答:“还解释不清。按说线索不能算少,开了枪,留下痕迹,与1990年‘12.19’案件并上了,特别是案犯眼部有主要特征,都以为非破不可,没料到进行了一个半月,还是没有结果,后来认为,他们急于搞到钱,没搞到,肯定还要作案,就暂时‘挂’了起来。”“侦查时的重要线索是什么?”“眼部的特征,格棱眼。根据两个人逃跑的路线和彻底消失的地域,划定了重点地区。所有符合基本特征的、尤其是有格棱眼的,全都经过认真排查,我记得当时筛出了二十几个嫌疑人,全都带格棱眼,都被请到向阳分局做辨认。我看是无一遗漏,但经过目击证人的辨认,全被查否了。”“那么罪犯也由此明白,他们中的一个眼部特征已被公安抓住,很容易暴露。”“是这样,当时全城都在议论格棱眼,还有几个人找到公安局来抗议。”王春林微笑地补充,很快又收敛笑容:“我也很奥秘,这个特征是遮掩不得的。临时遮掩更不可能。可以说罪犯除非经过公安部门的明确排查否定,很难避开群众的议论。为何被他混过去了,到现在也是个谜。”“由谁辨认?”“重要是小金鹤储蓄所的三个工作人员,他们都说得很肯定,能认出罪犯。”“也未必。大多数人不能可靠地辨认短暂接触的人,特别是在危急情况下。

我想主要的是,帆叶网,经过大规模的清查,这名罪犯和他的同伴都知道眼部特征是要命的,一旦出问题必须千方百计掩盖。”“你是说,他们很可能是‘1.28’作案分子?”李洪杰问。“体貌特征上也像,只不过进展到四个人,有了车,有了会开车的,开始杀人灭口,而且有了猎枪,还懂得了尽量幸免使用抢来的正规枪支--如果他们真是拿着一支‘五四’手枪闯入现场又不发一枪,那就是接受了小金鹤案件的教训。--当然,现在还只是推测。”落在小金鹤储蓄所外间地面上的两枚弹壳为瓶形,固定弹头的方式为卡窝紧口,壳长24.4mm,颈部直径为7.62mm,底座直径为9.9mm,无底缘,据此判明这两枚弹壳为:“五一式”7.62mm手枪弹壳。弹壳底面上标有“947”、“80”字样。在显微镜下观察弹底舌痕,其形态完整,边缘清晰,弹底窝凸凹线条痕明显,特性稳定。经验证,两枚弹壳是用工商派出所民警高连国被抢31082992号“五四式”手枪发射的。于是“1.25”案件发生后,1990年的“12.19”案件很快被牵涉进来,予以并案侦查。在一份由鹤岗市公安局市场治安派出所出具的“关于高连国被抢走的枪支证明”中记载:“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五时许,我所民警高连国下班回家途经矿务局选煤厂十道煤仓被杀。犯罪分子杀死高连国后,抢走他随身佩带的‘五四式’手枪一支,以及枪套和随枪佩带的‘五四式’子弹。被抢走的‘五四式’手枪号码为31082992。特此证明。”矿务局选煤厂占地宽阔,中心地带为车间、办公楼、机电房和浴池等设施。两旁有大型煤仓。煤仓两头开放,通进铁轨,平时常有装煤车箱停放。铁轨两旁挖有地沟,地沟上覆盖铁栅,铁栅距墙仅两块砖宽。仓库里黑洞洞的,走进去像步入山间隧道。发现尸体的是一名57岁的销售科工人杨xx,当晚17时10分左右(鹤岗此时天已全黑),他提着两壶开水从办公楼回检煤房,自厕所后的煤仓第十道地沟的小便门进入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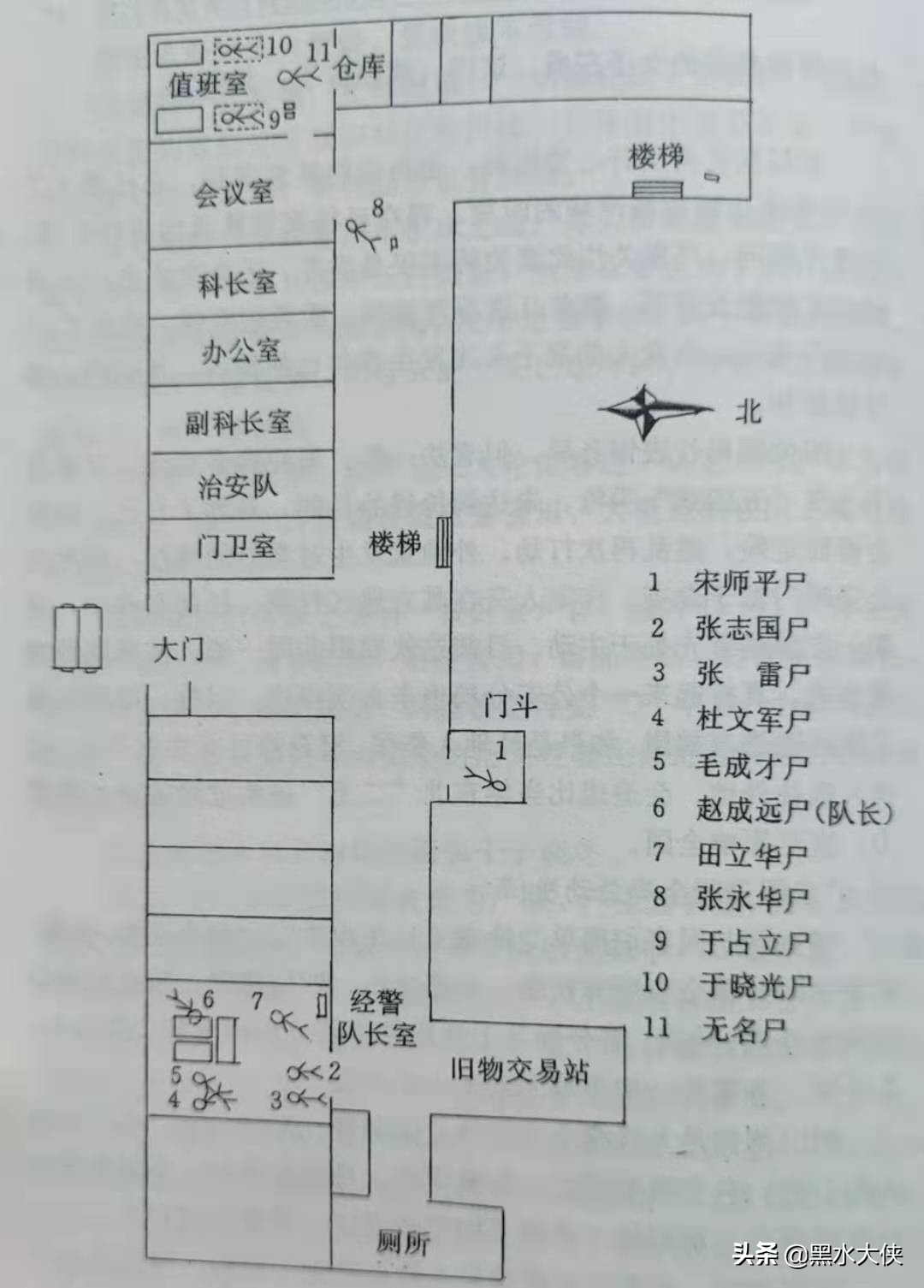
进门后看见门里侧暗处有一只方形折叠凳躺到在铁栅边缘。后来在证词中他说,当时他“并没有发现人”,但可以想象肯定有种异样的感觉震慑了他,因为凳子腿就搭在一具尸体上,而他没有凑近去看。杨xx提壶回到煤房,对54岁的班长陈xx谈了此事,两人拿着手电筒进第十道地沟。寻到原处,发现了地上躺着的人。人躺在一处墙垛下,头部靠墙,两腿内弯仰卧。两只折叠凳绑在一起,压在人的腿部,旁边还丢有一只栽绒帽子。两人看清此人头部流了不少血,显然是被人打的,便知出了大事,奔去泵房打电话。电话打给调度室,很快经济警察就赶到了现场。据陈xx说去打水是在17时10分左右。杨xx为抄近路,往返都经过十道地沟,但去时没有发现什么。情报上报到市局后,何文轩局长、李洪杰副局长当即部署勘查现场。勘查工作由20时30分开始,21时50分结束。仓房内被十几盏大灯照得雪亮,气温仍在零下20度左右。法医方面的负责人是伦江,他至今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尸体头下淌有血泊,并流向地沟。
大唐公主诬告大伯非礼自己,竟牵扯出谋反大案纪实:最后家破人亡
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
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的空印案纪实:明太祖朱元璋到底杀了多少人呢
所谓,指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文书而引发的一起著名案件。这个案子在当时为震动一时的大案,而在贪污腐败并不鲜见的当今社会也因其带有重典惩贪的色彩而常被人们所提及。 不过,这件案子在惩贪方面并没有多少成效,至多是君主猜疑个性的又一次滥用罢了。 当时有一个叫郑士利的生员,他说欲严惩空印者,是因为“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郑士利传》)。其实这里说得是客气了点。 很多史料记载,朱元璋发现了盖印空白文册的事时,反应是“盛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欺罔”。“欺罔”这两个字,不仅仅可以解释为空印者持空印文书欺罔百姓之意,更可以解释为空印者轻视皇权,也就是朱元璋的权威,私下偷懒,擅自盖印。 后一解释可能更贴近朱元璋的心理,因为关于空印案的不合理、不合法和它的坏处,郑士利上书朱元璋,讲得是非常清楚了,而朱元璋的反应仍然是“大怒”,根本不听劝,怀疑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反而将郑士利罚去劳改了。 这种对郑士利的猜疑,也正是郑士利以一个普通生员的身份上书指斥时事而触怒了朱元璋的一种反映。 空印案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规定,各地都需每年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才可结项。只要数字有一丁点儿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而且必须重新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因往来路途遥远,派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以备不时之需。这本是上知下晓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也从来没有哪个中央衙门发布命令禁止过。 但是,偏偏皇帝朱元璋不晓得。忽然有一年他发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大发雷霆,便严惩所有他认为有干系的地方官吏。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也被牵连在内而死去。方克勤的儿子就是后来因反对燕王而被诛十族的“天下”。 众所周知,明代洪武年间发生了许多大案,以十三年的案、十八年的案、二十六年的案最为知名。有人加上空印案,号洪武中四大案(如孟森《明清史讲义》)。 然而,其他三案发生的时间清清楚楚,没有异词,只有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却存在不同说法。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纲》都说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 这是两本较早的大学历史教材,使用非常广泛。近年新出的樊树志《国史概要》却认为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这是一本带有个人风格的教材,在大陆与香港深受好评,也多次印刷。 这三套教材的编写者都是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史学专家,而对于这样一件大案所发生的时间却记载歧异,不能不令人迷惑。(汤纲、南炳文合著《明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朱元璋传”均持十五年说。) 空印案发生在的手里,关于他的传记也应有所记载。有关朱元璋的传记,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明史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这本书吴晗曾经有过四次修改,前后经历了二十年,在史料上当是精益求精。 现在通行的就是最后一次的改本,这个改本由两家出版社印行多次,坊间均可见到。在这本传记里,吴晗指出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洪武十五年。这可能就是空印案十五年说的来源。 查手头常用的《辞海》(1989年版,1998年第17次印刷,印数近98万),有“空印案”词条,就写明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999年版2002年印《辞海》同此。)《辞海》中“空印案”条文很可能是参考了吴晗的《朱元璋传》。 从一个用词上可以得到说明。当时,户部要考核的名目,据《明史.郑士利传》是“钱谷册书”。在比《明史.郑士利传》更早的方孝孺所作《叶伯巨郑士利传》(以下简称《叶郑传》,收入《逊志斋集》四库本)里,这个名目作“钱谷策书”。 二者记载应该是相同的,但《朱元璋传》里则说是“钱粮、军需等款项”。“钱粮”约等于“钱谷”,“军需”是否等于“册(策)书”,就很可疑。(郑士利的上书中,先言“考校的策书是两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可比”,又言“钱谷之数必须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部,所以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官吏们往返户部与省府之间,“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势必耽误时间。在策书上盖印,可见策书或册书就是指登载钱粮的文书,户部要考核的也就是钱粮的数字,跟军需是没有关系的。) 在《辞海》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纲》、《国史概要》里都说的是“钱粮、军需等款项(事)”。由此,可以看得出吴晗《朱元璋传》的影响。 吴晗在叙述空印案的时候,也注出了材料来源:“《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郑士利传》。”殊不知,《明史》这两处记载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 《郑士利传》并没有直接记载空印案发生的时间,但可以推断出来。传中记载说,“时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叶伯巨传》就置于《郑士利传》之前,其中写道:“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 叶伯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了那封著名的上书,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气得元璋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关于这次星变的时间,明末谈迁《国榷》记载是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初,其他史料都没有异词。可以推定郑士利上言正是在洪武九年,这也就是空印案发生的时间。 方孝孺也在《叶郑传》明确记录:“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但是,在《明史·刑法志》里,于记载十八年后,追述了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随后又提及户部核查的名目是“钱粮、军需诸事”。可以想见,《明史·刑法志》可能正是如今空印案十五年说最初的来源。 《明史》本身的记载就有歧异,该何去何从?幸好还有其他史料以资考信。前面提及的明初好官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程贡和程的朋友杨御史诬陷,发到江浦劳改。服刑将满一年,本可释放回家,不巧发生了空印案,又被诬陷牵连了进去,于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 这些都出自其子方孝孺所作的《先府君行状》里,相信方孝孺不会连老父去世的日会记错。郑士利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星变求言之前就准备上书,则空印案早于此时发生,而方克勤自八年十月起在江浦劳改的时间将近一年(《先府君行状》原文是:“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 “终岁”就是“整一年”,不能理解为“年底”、“岁终”;古代中国人的计数法是包括起止点的,故从八年十月到九年九月恰为一年。),那么将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推定为洪武九年九月,是比较恰当的。 吴晗说十五年空印案发生的时候,恰好十三年胡惟庸党案还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辨。其实不然。《叶郑传》记载,“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郑士利后来上书,是持书到丞相府,由丞相将上书交御史大夫转达御前的。 这个丞相就是胡惟庸。以胡惟庸为首的朝廷官员不敢进谏,不是什么党案闹的,而是他们太了解皇帝的性情了,顶风强谏的话,岂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丞相还活得好好的,空印案自然就不会发生在洪武十三年之后了。十三年后,朱元璋宣布废除丞相这一官职。 另外,还有人认为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这可能跟《国榷》卷六的一条误载有关。《国榷》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条下记有怀庆知府林方徴(《明史》中作“方徴”)上言,其中说“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据此可推空印案在八年。 然《国榷》同卷又记空印事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则与前记林方徴事相矛盾,可知上言当在洪武十年。 关于空印案,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处罚了哪些官员?《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后来的处罚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 明代的省级地方机构有三个,即布政司(掌民政与财政)、按察司(掌司法与监察)和都司(掌军政),三司分权,互不统属。往下的地方机构府州县,都是由布政司这个系统下来的,跟其他二司没有关系。 按《明史.刑法志》的记载,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即地方上的监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 看来,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杀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袭旧称。 第二是到底杀了多少人?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这个数字同样可能是从《明史·刑法志》而来。 《刑法志》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说“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所言“过当”,也许即相当甚或超过之意。空印案也如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数,故吴晗云两案有七、八万人被杀。 然而,这个估计是成问题的。方孝孺《叶郑传》说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士原(《明史.郑士利传》中作“士元”),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官湖广按察司佥事。士原或即“行省言臣二十余辈”中的一个,幸而不是主印者,得以出狱。 郑士利在这些人入狱之初就想上书,后来为避嫌计,所以等到士原受杖出来后才言事,主要就是为留在狱里的那些死囚申辩。《叶郑传》文末说士利失败了,元璋“竟杀空印者”。贯通全文看,士原任官湖广,以从前的河南任内事牵连入狱,说明他是从湖广逮进来的,而朱元璋是按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顺藤摸瓜来捕人的。 等皇帝完成了大逮捕,也不过数百人。直到全文末尾,也不像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株连逮捕。而且,这数百人中,还有一些人被充军了。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所谓的数万之数,很可能是猜测类比之词(其他的几个大案确实杀人很多)。 退一步说,明初整个官吏阶层的人数不会太多,而跟空白盖印文书有关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朱元璋再狠,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人都杀光,弄得自己在中央做光杆司令。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说,洪武九年“空印狱起,官吏下狱者数百人”,这应该是实际情形。 郑士利对于空印案的申辩与批评,有以下几点: 第一,官方文书要有效,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而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印,是不能用来为非作歹的; 第二,钱粮之数,必须县、府、省到户部,级级往上相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一个确数,而如果“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那么就必须返回省府重填,势必要耽误时间,所以“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不足以怪罪; 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现在杀空印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第四,官吏们都是经过数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这么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 第二条提到“先印而后书”,也就是“空印”,《中外历史年表》说:“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 《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说,这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发运时的数字肯定跟户部接收时的数字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并不事先知晓,只有到了户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 所以,官吏们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就地填写实际的钱粮数字。 空印是沿袭的旧法,而朱元璋对元朝腐败的吏治是很痛恨的。固然元朝旧法可能存在易于作弊之处,但在郑士利解释得非常清楚的情形下,仍处死了所有的主印官吏,显然是很可见皇帝的专制性格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看法是:“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诚然如此。朱元璋在求言诏中是这样说的:“迩来钦天监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日思。 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於戏,于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 若假公济私,□(此处落一字)贤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有一个地方学官曾秉正上书,大谈如何“应天心”、“慰人望”以守成,《明太祖实录》抄了近六页,全是空对空的虚道理,朱元璋却听得很舒服,以为他是忠臣,提拔做了思文监丞。 叶伯巨和郑士利就事论事,坦坦直言,却引得皇帝大怒,以为叶伯巨离间皇家骨肉,以为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将两人下狱。 后来,叶死在狱里,郑跟他的哥哥士原罚到江浦劳改。还是那个曾秉正,后来也因言事忤旨而被罢官,穷得连回老家的路费也没有,不得已,卖了四岁的女儿,弄点盘缠。 看来还算是一个清廉自守的官。可这不行啊,把女儿卖了赚路费,岂不是给皇帝的统治抹黑,与朝廷提倡的孝悌之道相违背?也是一怒之下,皇帝将曾秉正处了个腐刑!这个曾官员后来不知所终。 原来,所谓的忠奸,也不过在皇帝的一闪念之间。皇权的专制权威是万万惹不得的。叶伯巨事先曾说:“即使没有皇帝的求言诏,我也要上书,何况现在正要求言呢?”都说言者无罪嘛,一个大皇帝岂能更是言而无信? 可是他偏落得个囚死狱中的下场。郑士利也是等得求言诏的机会去申辩,却根本不被理会。而所谓的空印案,也仅仅是皇帝所激起的一场小事故而已,是根本不值得当作惩贪除恶的标本案例去宣扬的。 为便于大家理解,小结如下: 一,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既不是洪武八年,也不是洪武十五年,而是洪武九年九月。此年有闰九月,又方克勤是在十月被杀,则空印案前后持续的时间约有三月之久。 二,空印案所诛杀的官吏人数并没有数万之多,而是区区几百人。空印案的规模跟洪武年间其他三大案是无法相比的。 三,空印案中被杀的官吏不仅仅是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还有按察司的官。 四,空印案中户部所核查的项目是钱粮的数字,并不包括军需等其他事项。 五,朱元璋之所以搞空印案,恐怕不真是从惩治贪污作弊出发,而是认为这些官吏背着上司、背着皇帝径直用空白盖印文书对付户部的核查是对皇帝欺罔的行为,后来郑士利的上书更是激怒了他,所以“竟杀空印者”,所以哪怕是他曾经最为欣赏的好官方克勤受诬入狱,也没有放过。 六,《明史》对空印案发生时间的记载存在歧异,而《明史·刑法志》可能是空印案研究上致误的主要来源;更早的记载方孝孺《叶伯巨郑士利传》、《先府君行状》当更可采信,可用以纠正诸多误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