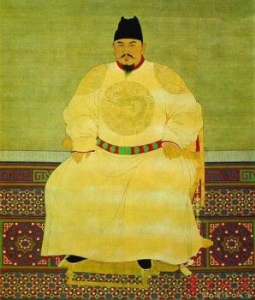手下有一个大将,名叫。
起初的时候雍正可是极其的宠信他,而年羹尧年轻时在雍正走向巅峰的这条路上没少出力,简直就是。

后来雍正出任CEO以后,就下令把年羹尧处死。
古代最忌讳什么人?不就是功高盖主和知道太多的人嘛,这些人简直就是当权者的眼中钉,没有用了直接找了借口把人咔嚓掉。
偏偏这年羹尧居然两样都占了,这不就是等于把脖子伸出去让当权者砍么。
网络配图 年羹尧想必知道的人很多。
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聪慧之人,起初是得到提拔和赏识,后来为雍正卖命。
你还别说,在雍正争夺皇位的这一路上,年羹尧那可是披荆斩棘无所不能。
雍正特别信任他,他也没有辜负雍正的信任,还将自己的亲妹妹送给雍正。
那个时候主仆两人简直好得没话,推心置腹。
雍正上任后,年羹尧的官就越做越大,聪明的人往往爬得快。
没多久他就掌握了全部的军政大权。
后来在西海大战中又立大功,雍正一看,哎,你又立功了,可是我没东西赏了,总不能把我皇位给你吧。
一想到皇位,雍正就来事了,这年羹尧是功高盖主啊,于是就开始防着年羹尧了,渐渐地猜疑越来越多。

没过多久,雍正就想尽一切办法非要弄死年羹尧不可。
那为什么雍正想砍了他呢? 有人认为,年羹尧不甘心做一个臣子,想自己做皇帝。
刚好不巧被雍正抓了一个现行,想做皇帝?先问问我答不答应,拖出去斩了。
于是年羹尧就被咔嚓了,自古帝王哪个容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半点挑战的,帝王最无法忍受得也偏偏就是这种人,合作时我们高高兴兴玩耍,成功后你也要眼色好自己隐退江湖得了。
来国杀功臣的皇帝历来还少么?网络配图 也还有人是这样觉得的,年羹尧之所以被杀那是因为知道得太多了。
当年本来康熙是要传位给十四阿哥的,跟雍正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当初十四身为扶远大将军,尽管手里有兵权,可是还是斗不过他四哥。
雍正于是串通自己的手下来了一场预谋,篡改了遗诏自己成为大BOSS。
据说十四没法发兵都是因为年羹尧的牵制,算起来年羹尧就是一个知道遗诏真相的人。
你想啊,雍正把这么一个“定时炸弹”留在身边放心么,万一哪一天年羹尧将事情的真相抖出去了,自己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诟病?想到这里雍正就一阵后怕,于是干脆找个理由直接把年羹尧做了。
但是也还有人持第三种说法。
这年羹尧是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案列,为什么这么说呢。
年羹尧自觉自己帮雍正当上皇帝就功不可没了,于是乎就开始放纵傲慢,居功自伟。
就连对待自己的部下都是极其的残暴,对老百苛,还经常帮助自己的亲戚找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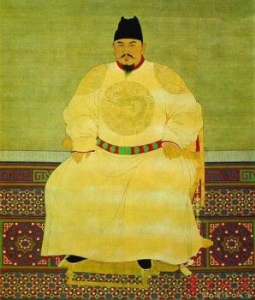
天下的老百姓愤怒了,雍正发火了。
你丫的居然这么想死,我成全你。
年羹尧死了,百姓开心了,雍正笑了。
网络配图 那么这年羹尧是怎么被雍正杀的呢?这还不好说,皇帝想弄死臣子,那借口理由还不是信手拈来。
雍正就利用了年羹尧的出生“吉祥物”砍了他。
为什么这么讲呢?据说当初年羹尧出生的时候带有白虎异相,恰好那时有一只白虎闯进了年羹尧的府邸,后来被打死了。
雍正一看,哎哟,时机来了,你年羹尧不是白虎出生么,现在白虎都死了你怎么还能活着呢。
于年羹尧就悲催了。
从历史来看确实是不知道年羹尧死于何因,但是就我们后人来看,其实雍正一早就想杀了年羹尧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最后年羹尧还是得死,这么一个臣子在身边估计是个皇帝都睡不着。
如今我天下已然太平,不杀留着做什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正德帝王朱厚照 人生为什么被称作一场玩笑
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
中国越是有当作的帝王为什么越担忧自己后事
在皇权运作过程中,为了维护国家体统,同时也是为了保障皇权的顺利运行,要求皇权须遵循国家现行体制的规范,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皇权之所以能够受这种限制,正是自身的运行机制和保障皇权的目的所要求的。皇权在运作过程中,常用对“后事”的担忧而能自觉地接受来自国家体制中的制约。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所谓的“后事”有两层意思。一是顾虑身后江山社稷的前途,再则是身后世人的评价,即青史之上的名声。越是有作为的,越是在这方面有着更强的自觉。像一代名君唐太宗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担忧。《贞观政要》一书中大量记载着的唐太宗对“为君之道”的探讨,其实很多都包含着这方面的意思。如《贞观政要》卷六《谦让》载: 贞观二年(628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唐太宗的这番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畏皇天,二是惧群臣(百姓)。对于群臣之惧,其实正可以从唐太宗之求谏、纳谏与对国家法令制度的信守等方面体现出来。唐太宗所以能成为史家艳称的善于纳谏的开明皇帝,正是基于所认识到的“常谦常惧”的为君之道。皇帝之求谏、纳谏,对于皇帝的行动自然要产生某些限制,特别对于有违现有典制刑宪的言行,群臣的谏诤往往能起到限制的作用。像贞观中太宗令选举中诈伪资荫不自首者处死,大理少卿戴胄据律定为流,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所谓“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不能因一时之喜怒而不顾法律之规定,最终唐太宗收回成命。应该说,谏诤对于皇权的随心所欲有所制约,但谏诤(谏臣)并不能从根本上制约皇权。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认为,谏诤对于皇权的限制,与其说是限制皇权的随心所欲,不如说是更有效地保证皇权的行使,因为谏臣所维护者乃是国家法令的尊严,维护法令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体制的尊严,就是维护皇帝的尊严,因为,说到底,皇权乃是国家体制的真正核心。皇帝对于群臣的进谏常视为“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裨益政教”,其实也无外乎关注其宗庙、社稷。贞观六年(632年)冬唐太宗行幸洛阳,途中即对等说:“虽帝祚长短,委以先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欲对谏官治罪时,近臣李绛就指出“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这样来理解谏诤对于皇权限制的实质也许就较为切题了。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皇帝对于群臣之惧就觉得并非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君王对于皇天的畏惧,与上述对群臣的畏惧是同样的道理。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灾异之变也往往能使皇帝引起警觉,反省理政当中的过失,减少施政当中的失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也能容易听从臣下的劝谏,天意、人事并非截然分开。由于皇帝之所敬畏者尚有一高高在上的天(上帝),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有了某种限制,甚至皇帝有时把自己的生命也与联系在一起,像临终前于洛阳所说“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更让人觉得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皇帝权力的至高无上,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天的意志与品格。也就是说,敬天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皇帝权力更加牢固,皇帝在郊天祭祀及封禅大典中的独特身分,使其权力与人格进一步地被神圣化与神秘化。“上畏皇天”的实质,与其说是对皇权行使的限制,毋宁说是使皇权更加神圣化。 除此之外,由于皇帝较多注意身后在历史上的地位及评价,所以在施政理政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也能有所节制。因此,修史制度对皇权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注重修史与,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按照古礼,设左史、右史,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隋唐时期,设起舍郎与起居舍人,职当左、右史之责,国家又设史馆,宰相往往监修国史,修史工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史官责任感较强,工作独立性较大。像所修起居注、实录、国史以及时政记等,都对君主具有规诫警示作用。 图片来源于网络 皇帝要想在青史留下好的名声,必然要注意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检点,做到谨言慎行。既然起居注、国史等所载会影响君王千载之后的声誉及评价,皇帝对于所载内容则是十分敏感的。唐太宗因为系发动夺储而立,所以,即位后顾虑史官对此事的记录,多次提出要看一看国史的记载,但分别为朱子奢、褚遂良等人拒绝,最后亲信只得顺旨,删削国史成实录进呈。因见所载玄武门事变之事“语多微文”,恐怕后世究其真相,于是以诛管、蔡而安周室为例相类比,要求史官重写,并美其名曰应当“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唐太宗为了自己能在后世留下一个好形象,不惜一改帝王不亲观国史的旧例,殊不知,他此举颇获讥于后代。 给事中、谏议大夫侍奉天子左右,职当规谏、讽议朝政,是朝廷谏官。给、谏兼领史官之职,使史官执笔载事之权有了更加现实的政治内容,史官载事对于皇帝行动的限制通过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谏诤等形式得以体现,无疑加大了对皇权行使之限制的范围与现实意义。贞观年间政治清明,与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很大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何种制度对皇权的限制,其实都更加有利于皇权的有效行使,因为,所谓诸种形式的限制,归根到底都是使皇权在行使过程中减少失误,而不是对皇权本身的制约或束缚。这与皇权运作过程中对“后事”的担忧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 就是说,皇权所接受的种种限制,正是自身得以巩固与有效行使的需要,是保障宗庙社稷永固、并获青史之上美名嘉誉的需要。大抵皇权行使过程中较能接受诸种限制之时,也是政治状况较为清明之世。贞观时期唐太宗较能注意纳谏、较能严格守法,所以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颇令后世称誉的,这一时期皇权行使当中的失误也较少;骄矜拒谏,举止略无节制,随心所欲,终致以万乘之尊,死于匹夫之手。两相比较,皇权之接受限制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后仍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对皇权的何种性质与何种形式的限制,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皇权,是出于使皇权更加有效行使的需要。不同形式与内容的限制,从根本上要服从于皇权意志,这些限制绝不能超越皇权、冒犯皇权的尊严,唐太宗以魏徵“每廷辱我”而欲杀此田舍翁。甚至如唐太宗亲观国史,更能反映出皇权意志是可以凌驾一切的。元和初年任左拾遗的翰林学士,曾因论事之际,直言“陛下错”,唐宪宗大为恼火,认为是“白居易小臣不逊”。 据《》卷一六六《白居易传》载唐宪宗所言,则为“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这很贴切地说明,即使是谏官,论事之际也不能冒犯皇帝的尊严,无礼不逊之辞,是会令帝王难以忍受的。因此,对皇权的限制种种,都须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和这一范围之中,对皇权的限制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超越这一条件和范围,对皇权的限制与束缚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