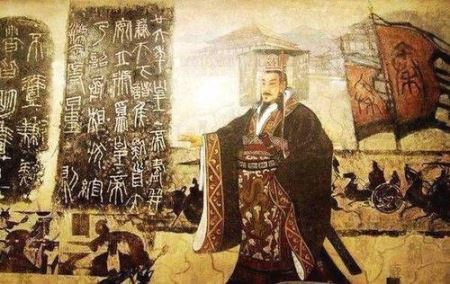王敦之乱中王敦真的有不臣之心吗 可能只是咽不下那口气而已
司马睿与兄弟,乃至士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

为自己的弟弟深报不平,他上疏司马睿,望司马睿能够宽容王导犯下的过错,令其将功补过。
王敦这份上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前秦统一北方后,与东晋对峙的地图 然而司马睿收到这份上疏后,对王敦却更加忌讳了。
他连夜将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召进宫,与他商议对策。
司马承顺承帝心,对此表现得十分愤慨,说:“陛下当初没有早点遏制王敦的势力,以至于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
王敦一定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刘隗更是在一边煽风点火,让司马睿派遣心腹出镇以提防王敦。
恰好此时王敦表请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为湘州刺史,司马睿顺势命司马承出镇。
司马承万死不敢推辞,然而行前的一番话已预示了他将来的结局。
他对司马睿说:“湘州经历蜀寇,民物凋弊,如果我过去,一定要三年才能参加战事,如果不到三年,即便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果然,司马承到了武昌以后,王敦设宴款待他,对他说:“大王知书达理,恐怕并非将才。
”司马承在司马睿面前底气不足,面对王敦时却表现出十分傲气,他对王敦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将才呢?即便是铅刀,也有一割之用吧!”这样的夸口,在久经战事的王敦面前未免显得有些可笑,因此王敦也并不在意,对心腹钱凤说:“他没有真正带兵,并不知道战场的可怕,不知恐惧而学人讲壮语,可见他也没什么能耐,实在不足为惧”。
因此便听之任之了。
司马承的任命于江东大局其实并无十分影响,真正引起后来整个东晋局势变化的,恐怕正是司马睿在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以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的军事任命,“名为讨胡,实备王敦”。
尤其是戴若思都督豫州军事,令原豫州刺史十分不满。
他用尽一生心血经营边疆,终于换来了十余年和平,而这一切全都要交由戴若思接管,祖逖“意甚怏怏”,又知道司马睿这次军事任命,实际是为了防备王敦,北伐就此不遂,因此悲愤发病而死。
王敦虽然擅自任命官吏,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史料而言,除却史书评价说他有以外,并无任何实际事迹表明王敦有逼宫之嫌。
而当戴若思、刘隗出镇时,王敦开始也是从大局出发,写信给刘隗说,“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
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希望刘隗不要这样步步相逼;然而刘隗不愧是政治上的矮子,断然回信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竭股肱之力,效力以忠贞’,吾之志也”,以王敦心气之高傲,此时又手握重兵,先有司马承出镇湘州,后有戴若思、刘隗出镇司、青,刘隗,王导在朝中被司马睿所猜忌疏远——是可忍孰不可忍?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于武昌起兵,上疏司马睿,要求杀掉刘隗。
这一次,他的上疏中带了十足的威胁之意,“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大有你不杀刘隗,我就不退兵之意。
到了芜湖,王敦再次上表,不过这次针对的目标是刁协。
司马睿终于被王敦激怒,声称要亲帅六军诛讨王敦,能够取王敦项上人头的,封五千户侯。
朝臣们很快做出了选择。
仆射周顗的态度可以说是代表了朝中大多数人的态度。
太子中庶子温峤就王敦起兵这件事问他,周顗说,皇上不是尧舜,当然会有过失,做臣子的怎么能够举兵相胁呢!一方面,他们认为司马睿的确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然而作为臣子,王敦只能劝谏,而不能举兵相抗。
也因此,在王敦之乱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的人其实很少,大部分人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
响应王敦的,大多是琅琊王氏子弟,和王敦的心腹宠信。
比如少时就酷爱兵书的沈充,以雄豪闻于乡里,被王敦引为参军,与同郡钱凤一起深得王敦信赖。
因此当王敦举兵内向时,沈充立刻在吴兴起兵,王敦以其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的兄长,光禄勋王含乘舟逃奔王敦。
与此相对的,是谯王司马承与梁州刺史甘卓的拒绝。
司马承的拒绝很好理解,他原本就是忠于晋室,此番出镇乃是司马睿的授意,因此当王敦让参军桓罴前去长沙将其请为军司,司马承坚决不从,但却也知道自己势力单薄,不是王敦的对手,不免有“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得死忠义,夫复何求”的感慨。
而甘卓的考量就要复杂得多。
他之前因为多次参与平叛,因功被封为湘州刺史,后迁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
其在任期间,免除税收,让利于民,宽政简惠,深得称赞。
王敦起兵后,曾希望甘卓能与自己一起发兵,但甘卓犹豫再三,终究还是拒绝,他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发表檄文,说王敦谋逆,应加以讨伐,又联合,并命参军邓骞、虞冲至长沙,让谯王司马承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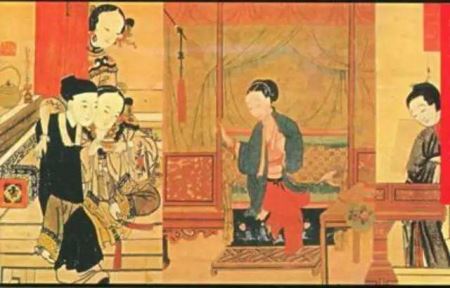
甘卓之所以拒绝,并非为朝廷考虑,而是权衡了司马睿与王敦势力孰优孰劣后作出的决定。
因为各方都积极响应甘卓,“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因此即便是王敦,心里也有些惧怕;刚好甘卓犹豫不定,屯兵猪口,王敦便派其侄儿甘仰求和,对甘卓说,“你这样选择,是尽臣节,我不会责怪你;然而我王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这样做”,希望甘卓能班师回襄阳。
司马睿 另一方面,王敦继续行军建邺,司马睿急召戴渊、刘隗入卫京师。
刘隗回到建邺后,与刁协一起力劝司马睿尽诛琅琊王氏,然而也许司马睿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真的对王家痛下杀手,只是恼恨臣强主弱的局面;而此时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且不说他没有能力诛杀王氏,即便他有,一旦他尽诛琅琊王氏,天下士人必定寒心,且江东豪族绝不是他与刘、刁诸人所能制衡的。
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司马睿没有同意。
王导对此并不知情,见王敦起兵,他心忧如焚,率领族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天早上跪在宫门外待罪。
司马睿的立场原本就已经动摇了,再加上周顗的劝解,便命王导入宫觐见。
王导十分惶恐,还不待司马睿说话,就不停磕头谢罪,说“没有想到竟然出在了臣的家族”!唯恐司马睿怪罪更甚。
司马睿对王导的话,其实是半信半疑的。
他虽然“跣而执其手”,光脚下阶,拉住了王导的手,然而却将王导任命为前锋大都督,要他大义灭亲,前去讨伐王敦;同时,以征虏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自己亲着戎装,率兵屯守郊外。
王敦到了建邺以后,原本想先攻刘隗,然而其部将杜弘却劝他说,刘隗死士太多,恐怕不容易拿下,不如先从周札攻起,因其“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
王敦同意了,于是转攻周札。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札“开门纳弘”,王敦不战而胜,成功入据建邺。
究其原因,可以稍加推测。
周札素有脚疾,“不堪拜,固让经年”,而却被有司弹劾,不得已只好前去视职。
而史册所载的有司,按当时朝中局势而言,不是刘隗就是刁协诸人,因此周札之叛,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王敦进入建邺后,并没有感觉到丝毫胜利的喜悦,反而十分感慨地说:“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我如今起兵,虽然号称是清君侧,但不免会被当做逆臣,再也不会有什么建功立业,盛名远扬的机会了。
虽然这样感慨,但王敦拥兵不前,放任士兵到处劫掠财物,宫中诸人纷纷逃散,仿佛是无声的示威。
司马睿原本命刁协、刘隗、戴渊、王导等人连续出战以攻建邺,在几番战败后,他也丧气了,脱下戎装对左右说:“如果王敦想要我这个位置,早点说不就好了?何必要将百姓拖累到这样的地步呢?”一句话轻轻巧巧地便将前因后果全部撇得干净,仿佛王敦是因为早就觊觎帝位才起兵的。
他又遣使对王敦说,如果你不忘晋室,那就息兵吧,这样天下或可安定,否则的话,“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
后人多以为王敦狼子野心,才将司马睿逼到这样的地步,然而联系前后因果,可知王敦这次起兵,的确是不满刘隗、刁协干预朝政,小则损害琅琊王氏的利益,大则动摇江东豪族拥立之心,绝无不臣之意。
而司马睿对王敦这样说,其实也是威胁十足,如果不就此退兵,那么图谋这顶帽子,王敦就戴定了。
也因此王敦退兵,司马睿以其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都没有接受,但杀掉了协助司马睿的戴若思、周顗,刁协在逃跑路上为人所杀,送首于王敦;而刘隗则携妻子亲信投奔了,石勒以其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再次体现了刘、刁二人之无有骨节。
而得知了戴若思、周顗死讯的甘卓,方寸大乱,不久就为襄阳太守周虑所杀掉了。
虽然《》记载说,当初四方劝司马睿称帝的时候,王敦就已经有不臣之心,想改立其他王储,因为王导不同意而作罢,然而还是那句话,评论不足为据,没有任何切实的事例能够表明那时候的王敦想要取晋室而代之。
但这次变乱却也让王敦反过来思考一脉是否值得拥护。
他责备王导没有听从自己的话,改立他人为帝,以至于现在差点被灭族,这句话虽然真假也有待商榷,但“几至覆族”的后怕,一定萦绕在王敦心头,成为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更何况,王敦清楚地知道,即便很多人与自己的立场相同,但出于各种考量,多数人现在对自己的定义,无怪乎“乱臣贼子”四个字。
譬如周顗死前经过太庙,大呼“贼臣王敦,顷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祗有灵,当速杀之”!其族弟王彬在凭吊周顗后,勃然怒斥王敦屠戮忠良,欲谋不轨,祸及门户等等。
大概也有些破罐破摔的意味,王敦渐渐起了谋废立的心思。
他原本想废黜太子,重新迎立东海王司马越的后裔与裴妃,然而因为温峤直言相抗,群臣以沉默表示反对而作罢。
然而此时的王敦,兵权在握,其实也不太在乎朝臣的意见了。
他以西阳王司马羕为太宰,加王导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进行了一次军事、行政大调动,“转徙黜免者以百数”,十分恣意。
谢鲲劝他说,您虽然诛灭佞臣,建有功勋,但入朝以来,一直都称病不去面圣,若是能去觐见天子,君臣释然,一定人情所归,天下尽乐。
王敦反问谢鲲,你能保证不发生什么变故吗?纵然有谢鲲的保证,但王敦根本不信任司马睿,终究还是没有觐见司马睿,带兵返还了武昌。
但司马睿经过此事后,忧惧成疾,不久后就去世了。
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

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敦变得渐渐和从前不一样了。
他“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
虽然史载其所任用的沈充、钱凤凶险骄恣,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但就史册而言,跟随王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沈、钱二人“凶险骄恣”的实证。
相反,这两人对王敦相当忠诚。
尤其是沈充,当晋明帝准备讨伐王敦时,曾让其乡人沈祯前去劝他,许诺事成后将他提拔为司空,也许是对晋明帝的不信任,然而毕竟沈充宁死,也不肯折节背叛王敦。
反倒是王敦自己,脾气越发暴虐易怒了。
当时高官督护缪坦想将武昌城西地作为军营,太守乐凯劝谏说,这块地是百姓用来种菜的,不应该将其夺走。
王敦听了大怒,说:“若不是我来这里,会有武昌这个地方吗?人们说这里的土地都是我的!”乐凯不敢再说,最后还是郭舒不畏王敦,委婉进谏,王敦才将地还给了百姓。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因此这时《》中对他的评价,“多害忠良,宠树亲戚”,也不可谓不客观了。
王敦之乱 除此以外,王敦还让朝廷征召自己,以谋更大。
晋明帝心思慎密,是为深谙权术的,不欲与此时兵力强盛的王敦相抗,因此从善如流,手诏征之,加黄钺、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暗地里却在谋划如何削弱王敦的势力。
虽然他曾想以流民帅郗鉴的势力为外援,自己又亲自前往王敦兵营查看地形,但这一切都比不上中书令温峤的无间道效果好。
王敦曾以温峤为左司马,温峤事事配合,深为王敦所重,并假意结交钱凤,称赞他说“钱世仪”。
温峤向来品藻人才闻名,得他一赞,钱凤也对他十分倾心。
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六月,王敦表情温峤为丹杨尹,希望他借机监视朝廷动向。
温峤临走前,假装酒醉冒犯钱凤,以至于他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此人与朝廷往来过密,不能信任”的时候,王敦反而指责钱凤不应该为了温峤酒醉冒犯的事而耿耿于怀。
当知道温峤背叛了自己以后,王敦大怒,写信给王导说要将温峤抓来拔掉他的舌头。
然而此时的王敦,无疑心有余而力不从心了——他已经病到了钱凤直接问他后事如何的地步了。
王敦知道自己若是病死,手下人必定成不了大事,便以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给了钱凤三条建议,“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然而钱凤政治才干也十分堪忧,认为王敦所谓的下计,乃是上上之策。
与此同时,晋明帝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硃雀桥南诸军事,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领左卫将军,吏部尚书卞壸行中军将军。
又诏征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
王导听说王敦病入膏肓,帅琅琊王氏诸子弟为王敦发丧,以至于众人都以为王敦已经去世,顿时斗志昂扬。
不得不说,没有王敦带领的军队,其实与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晋明帝手下诸位将领,皆是一时才俊,因此王敦部众节节败退。
当听到自己的哥哥王含战败的消息时,王敦大怒,但同时也明白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了。
他本欲自己出征,毕竟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只好告诉少府羊鉴与王应说,等他死后,“先立朝廷百官,然后营葬事”。
说完后不久,王敦就去世了,时年五十八。
王应的确没有发丧,他所做的,是用席子将自己养父的尸体草草裹了,在外边涂上蜡,埋在厅堂下面,与诸葛瑶等日夜纵酒淫乐。
不久,王敦部将俱被击溃,而王敦的尸体也被挖出来,“焚其衣冠,跽而斩之”,与沈充的头颅一起挂在城南朱雀桁上示众,若不是后来朝廷许可,甚至都没有人敢为他收尸。
王敦一代英雄豪杰!若泉下得知,不知作何感想! 东晋初期的这一段历史,我反复阅读,总觉得十分困顿;中间又与朋友探讨过很多次,却仍然无法确定,王敦是否真有谋篡之心。
我相信他最开始被迫举兵内向以捍卫自己乃至琅琊王氏的利益,是确然的清白无辜;然而后期的他暴虐恣意,与那个酒醉后一边吟诵乐府歌“骥伏枥,。
”,一边以如意击节唾壶的漫不经心男人已不再重合,我无法再在有限的史料里揣测他的真实心意。
也许时光与政治真的改变了太多东西,很多时候,一步错,步步错,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而我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这千百年后读史的时候,感朝政之炎凉,笑人主之猜防,哀为臣之局促,惜英雄之末路而已。
王敦,这样一个个性强烈,断不肯受半分委屈的人,终归为了争那一口气而背上了千古骂名,落得个死后戮尸的下场,其生之恣意,也幸,其死之凄凉,也不幸,然而——半生痴狂半生笑,心绪尽付纸上尘,这一切,到底是与他无关的事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