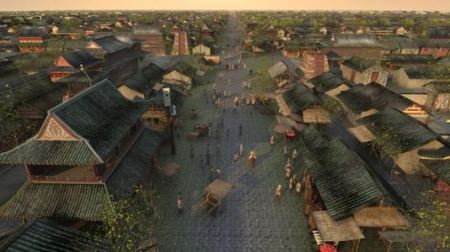提到“”,我们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戏弄的场景,但是另外两个藩王我们却几乎没什么印象,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南王尚之信。
尚之信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爵位,尚之信从小就跟随父亲到处征战,后来尚可喜判明降清,还亲自出城迎接了尚可喜。
后来也对尚可喜礼遇很高,把他封为平南王。
而尚之信也成了的藩二代。
但是尚之信和他父亲不同,虽然跟随父亲征战南北,但却没有一点军人家庭的风范,反而从小恶习不断,残暴贪横,十分不成器。
而这一点,尚可喜的军师也多次告诫尚可喜不能把爵位交由尚之信继承,建议另选继承人。
而朝廷内也都知道尚之信的恶名,目中无人难以掌控,一直都不想让尚之信继承平南王的爵位。
尚可喜也看出了朝廷的意思,就又向朝廷上奏,请求让次子尚之孝袭封,也准许了。
这样一来,想当藩王想疯了的尚之信就对朝廷心怀不满。
正在这时,吴三桂势力越来越大,朝廷派尚之孝去退敌却战败。
尚可喜也卧疾,朝廷只好把藩王事务交由尚之信打理。
吴三桂看出了尚家的权力斗争,就派人策反尚之信。
尚之信果然倒向吴三桂,还把重病的尚可喜关了起来,夺了弟弟尚之孝的兵权,最终把尚可喜活活气死了。
再后来,尚之信和吴三桂爆发冲突,谁也不服谁。
尚之信就再一次出卖吴三桂,投靠了朝廷,想借此向朝廷表忠心,保住自己藩王的地位。
对于尚之信的归顺,康熙当然十分欢迎,但是也没有盲目信任。
康熙帝先是表彰了尚之信,也准许他袭平南王爵位,尚之信十分高兴,派人向朝廷献上重礼。
康熙借此下诏说:你这次功劳不小,不过这种破财的事情就免了,以后老老实实做人,朕就很开心了。
老老实实做人,说着容易,对于尚之信这种纨绔子弟来说难比登天。
后来康熙多次命令他出兵,他都各种找理由抗命不从。
同时,他还在自己的地盘肆意妄为,动不动喝酒杀人,还随意处置康熙派去的大臣。
最终,被康熙拿下赐死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土屋昌次:武田信玄的“奥近习六人众”之一
土屋昌次(1544-1575)是金丸筑前守虎义的次子,幼名平八郎,武田信玄的“奥近习六人众”之一,武田家年轻一代里的猛将,对野战和城战都出众的才能。 土屋昌次是金丸筑前守虎义的次子,幼名平八郎,武田信玄的“奥近习六人众”之一(另外五个是三枝守友、武藤喜兵卫、甘利昌忠、曾根昌世和长坂源五郎),武田家年轻一代里的猛将,对野战和城战都出众的才能。 土屋昌次的初阵就是第四次川中岛合战,当时他年仅十七岁。在这场战役中,他表现异常活跃,负责守卫信玄的本阵,毫无惊慌失措,在上杉军的猛攻之下,始终不曾后退过一步,他的武勇连信玄也为之感慨。这场战役之后,昌次因功被信玄要求继承武的名族土屋氏并正式改名为土屋昌次。 在三方原合战中,土屋昌次接受德川氏大将鸟居元忠的一骑讨,并且击败了鸟居元忠,因此而得到了双方的赞扬。 土屋昌次是信玄近侍出身,对信玄十分忠诚。在信玄病死之后,曾意欲殉死追随信玄公而去,但是为弾正忠正高坂昌信所劝。(当时高阪昌信不也总想自杀殉死么……) 长篠合战中,土屋昌次和穴山信君、马场信房、真田信纲、真田昌辉、一条信龙率领三千骑兵的武田军右翼队。面对织田信长的三千支铁炮,昌次所在的部队虽然突破了第二道防马栅,但还是被铁炮挡在了最后一道防马栅之后。5月21日下午1时,昌次在随山县昌景一起突破马防栅冲锋攻击时,两人均遭铁炮击中身亡,昌次时年仅三十二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帝王毒誓不可信:风流皇帝乾隆为什么忤逆雍正生前旨意?
咱们国人有一种圣旨崇拜,认为皇上开了金口,就是玉律。有故事传说时节,湖南有个在长安做官的人想为家乡做件好事,便在每日出行的路上用蜂蜜写了一行字“澧州粮米可免”。皇上那天出来看到密密麻麻的蚂蚁在那行字上爬,信口念道“澧州粮米可免”,那湘籍官员“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立刻“谢主隆恩”。据说皇上非但没有办他捉弄之罪,而且兑现承诺,不再收澧州粮米税收了。此种佳话多矣,可信度有多高呢? 的金口就信不得。雍正不但空口无凭,他信誓旦旦写的保证书,甚至他指天画地发的毒誓,也多半不可信。 雍正初年,湖南有个小秀才曾静,不知道哪根神经短了路,突然想起造反来了。他听说有个后代名者,在川陕当总督,权力很大,而且拥兵十万,他就臆想开了:岳钟琪是民族英雄之后,而所谓民族英雄者,实是汉民族之英雄,只会忠汉统,不可能忠满统的。在这臆想推理中,他写了一封造反信,效仿骂,骂雍正弑父杀兄,夺母占媳……总结了八罪十罪的,总之是把雍正骂得一团糟,简直不齿人类,狗屎不如。 曾静这案子几乎众所周知,不说也罢。有意思的是,雍正对这案子的处理。也许严重的问题确实是教育群众,雍正把进行一番思想改造,硬把他给“教育过来”了,不杀他了,而且派遣曾氏到全国各地去宣讲政策,现身说法。犯了如此造反大罪与骂君大罪,每一罪都够曾氏死一千次,难道真不杀了吗?不但曾氏惶惶不可终日,而时人也是多有疑心的。这时候,雍正放下身段,向曾氏、向群众写起保证书来了:我发誓,我绝不杀曾静,而且“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杀戮”。 这话放在雍正时是天宪,放在其子乾隆时是祖宪,都是铁书写死了。看来曾氏应该是“改了就是好同志”的了,睡到自然醒、活到自然死没什么问题的了。然而,言犹在耳,乾隆一上台,就完成他老爹没完成的“恨事”,把曾静拉到菜市口,“咔嚓”一声割了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切齿之状,宛然在目前。 誓言大概也是分档次的,根据兑现的自觉程度,也许可分为诺言、誓言、毒誓吧。骗你是狗狗,骗你……这样的誓言才有点发誓的样子。雍正给曾静吃的那颗定心丸,介于诺言与誓言之间,采信度不高,也是自然。可是,雍正发了毒誓,就一定可信吗?未必! 雍正接之班,有所谓“传位于十四子”的野史传说,这个事情真确与否,实难断言,但是,雍正上台,靠的是与隆科多等几个心腹大臣,那是连雍正也承认的。年羹尧对雍正恩莫大焉,要是市民之间的话,雍正早该垂泪下跪,对着谢“再造之恩”了。确实,年氏对雍正不但有扶植之恩,而且有保其江山之勋。雍正初登大位,青海发生叛乱,年氏奉命出征,一举平息。年氏南征北战,为雍正尽犬马之劳,雍正对他感恩戴德,非比寻常。 年氏有次又要出征,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有点踌躇。雍正见之,不是臣子向皇上表忠心,而是倒了一头,皇上向臣子发誓了:“尔此番出征,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看看,拿天拿地拿神明说话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人民也。”读到这段话,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一口一个朕字,那么,没几人相信这是皇帝在说话,倒像山野草民市井小民在那里赌咒:我肯定不会对不起你,如果对不起你,我当你的儿子;如果我的儿子对不起你,那不是我养的儿子,是狗娘养的儿子!他不但将自己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全国人民都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子孙万代都拉在这誓言里。这都是当着天发的,当着地发的,当着三尺头上有神明发的,实在不是一般的誓言了,是很毒很毒的毒誓了。 其实,雍正在发这番毒誓之时,他已经准备对年氏下毒手了。年氏自恃,越来越不像话了,,唯我独尊,将权柄操持己手,大有逾制之处。年氏吃饭叫做“用膳”,请客叫做“排宴”,接见部下叫做“引见”,送人东西叫做“恩赐”,有皇帝那般排场了。不但臣子向雍正告阴状,雍正自己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万事俱备,只欠时辰,时辰一到,就举屠刀,杀无赦!雍正上回处理曾静,交给子孙去办,为什么?因为上回他没发毒誓;这回就不给后代出难题了,让子孙担起毒誓,总是不好的,他就负起全责了。 也曾给帮他打天下者发过许多免死铁券,但他想杀谁不是照样杀了?皇上的金口可信么?皇上的圣旨可信么?皇上的毒誓可信么?皇上的铁券可信么? 再举个小例:几乎所有皇上,其在台上台下都喊过“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的口号,都刷过“从来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的标语,都做过“导民务为第一要政”的文章,一副群众利益至上、以民为本的模样,到头来看,践诺者有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