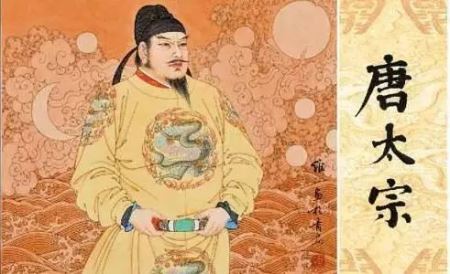《灵魂摆渡人3》热播,热爱IP剧的各位看官们,异常的激动,夏冬青真实的身份终于要被披露出来。
一个点背异常的穷苦屌丝原来是千年前战败的转世容器,被各路神仙厉鬼戏弄设卡艰难的存活人间。

由于中蚩尤战败,其身已死。
蚩尤的灵魂妄图霸占容器夏冬青,并对千年前的战败心怀怨恨,希望清洗后代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冥帝神茶与昆仑分各怀鬼胎在夏冬青身边各自安插眼线。
神茶妄图让蚩尤重现人间,昆仑的那群神仙们则更多的想要夏冬青身死让蚩尤没有转世的机会。
然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那场涿鹿之战。
网络配图从剧中我们了解到,涿鹿之战中黄帝联合部落,与南方的蚩尤部落开战,战争双方都请来神仙帮忙。
黄帝有九天玄女、女魃、应龙等,蚩尤有冥帝兄弟(也就是神茶和郁垒),风伯雨师等。
最后蚩尤战败了,炎帝和黄帝部落合并,所以我们才有了“炎黄子孙”的名称!冥帝共有两位,神茶和郁垒,蚩尤战败被擒,才被任命管理地府。
虽然,剧中有一定的改编,但是华夏文明的历史中的确记载了涿鹿之战,只是这一战,是黄帝联合了炎帝部落,打败了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
黄帝斩下蚩尤的头,接管了九黎部落。
此后,才开始慢慢形成中华文明。
然,真实的涿鹿之战到底是怎样的?《逸周书》记载:蚩尤驱逐赤帝(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
《·大荒北经》中记载:蚩尤作兵攻伐黄帝,黄帝令应龙迎战,双方在冀州之野大战,蚩尤兵败被杀!网络配图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涿鹿之战发生在冀州之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境地儿。
千年前的,那里应该是一片蛮荒,人烟稀少。
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自白书。

不管在《灵魂摆渡人》中还是在众多记载和传说中,蚩尤都是被丑化成一个可怕的魔鬼,一个争强好胜的杀神,一个原始部落中野蛮成长的大酋长。
由于历史久远,很多传说多数是被杜撰而来,其结局没有什么真实性。
事实上,涿鹿之战的发生,并不是蚩尤的好斗而引起,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实际要比炎黄部落发达的多。
蚩尤一族属于九,也就是东夷一族,此族的生活栖息地应该在如今的山东一带。
山东自古都是文明的发祥地,更是孔孟的诞生地。
可见,东夷之地在很久远之前就孕育着文明的火花。
《世木·作篇》记载蚩尤“以金作兵器”,也就是说蚩尤部落那时候已经掌握了冶炼技术,进入了青铜或铁器时代。
而黄帝部落那时候还处在石器时期。
所以,黄帝最初在和蚩尤的战斗中一直处于下风。
传说黄帝,“九战九不胜”最后乃不得不求救于九天玄女,九天玄女帮助黄帝一起打蚩尤,这才取得战争胜利。
还有一个传说是黄帝有指南车,能够辨别方向,而蚩尤部落则不知地形,迷失方向,因此被黄帝打败。
台湾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一书中记载,蚩尤部落当时的文明发展程度要比黄帝部落高。
而此书,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由台湾三军大学组织编写的,并由经钱穆、王云五、陶希圣等著名学者校订指导,历时十余年编成,其书内容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网络配图书中记载,涿鹿之战场面惨烈,有兵刃加身的蚩尤一族始终占据上风,黄帝部落不断后退。
直到涿鹿之地附近,黄帝利用地形的优势,把蚩尤族层层围困。
《中国历代战争史》认为是黄帝拥有指南车才能掌握地形的优势。

然则,古书中记载,在涿鹿交战之际,偏偏又刮起一阵莫名其妙的大风,飞沙走石,大雾弥漫,蚩尤不辨方向,而黄帝有指南车相助,最终取得胜利。
战争三利器:天时。
由此可见,黄帝的胜利更多的与文明的先进无关,最终的天时便是他取胜的最终因素。
古书《龙鱼图》云:“黄帝,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
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
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
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
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
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从中可得,蚩尤在民间的威慑力那真是杠杠滴,如果这老人家不是战败被杀,那战斗值甩啊、啊多少条街,神一般的男子就是不一般。
所以这黄帝仅凭杀蚩尤便可威慑天下。
成王败寇,如不是那场大风,也许今日我们会不会自称“蚩尤子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清代蒲松龄简介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生平
蒲松龄简介: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辈蒲生,做过玉田知县,即《·梦别》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 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己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然而,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幕宾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贫病交加 笔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欧阳修竟然写“小黄词”?《醉翁亭记》背后隐藏了一场“不伦之恋”!
竟然写“小黄词”?《亭记》背后隐藏了一场“不伦之恋”!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每个朝代的官场都充满明争暗斗。自古以来,文官之间的攻讦有一种惯用手段,就是从对方所写的诗文中挑刺,以证明作者的政治立场或生活作风“有问题”。仅北宋一代,就有两位名臣先后中招,一位是欧阳修,一位是。苏轼是因为写诗“讥刺”变法,被政敌构陷下狱,酿成“”。相比之下,欧阳修虽然没坐牢,却比苏轼更难堪: 他因为一首“小黄词”,竟被卷入到一场莫须有的“不伦恋”中。 “词”这种文体,最初多写男女间的,由歌女配乐演唱。一面认为词不登大雅之堂,一面却又对填词情有独钟。最奇怪的是欧阳修,此老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一面大力宣扬“文以载道”,一面又填了不少污力十足的“小黄词”,其中一些文字之香艳露骨,让人脸红心跳。比如《醉蓬莱》:“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写女子偷欢时的紧张,“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写幽会后意犹未尽,惦记着花前月下“再来一次”;又如《蕙香囊》: “宝檀槽在雪胸前,倚香脐、横枕琼臂”; 还有《蝶恋花》:“几叠鸳衾红浪皱,暗觉金钗,磔磔声相扣”…… 就算不懂词的人,单看这些“雪胸”“香脐”“叠鸳衾”“声相扣”的字眼,也会有“开车”的既视感吧。 大概是因为才华出众,官声又好,欧阳修的多数小黄词, 基本都被当时的文人圈视为游戏笔墨,酒宴时让歌女唱唱,乐呵乐呵就得了,很少有人去对号入座,也没觉得欧阳修的“作风”有问题。 直到一首《望江南》,让这位词坛“老司机”差点翻车。 那年的开封府审理了一桩通奸案:欧阳晟之妻与家中男仆私通,事败见官之后,张氏不仅对奸情供认不讳,竟还供出了婚前的一段“不伦之恋”:自己小时候寄住在舅父欧阳修家时,舅父对自己常有一些暧昧之举。 欧阳晟是欧阳修的堂侄,这个张氏虽然名份上是欧阳修的外甥女,其实是欧阳修的妹夫张龟年与前妻所生,欧阳修的妹妹只是她的继母,所以她和欧阳修并无血缘关系。后来张龟年病故,继母就带着她投奔欧阳修。一直等到张氏长大成人,欧阳修便以舅父的身份主婚,把她嫁给了欧阳晟。 至于张氏为何要在此时指认欧阳修曾对自己“不轨”,一种可能是出于无知和恐惧。张氏投奔欧阳修时只有七岁,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男性长辈,加上当时保守的观念,她把舅父一些正常的亲昵视为调戏是有可能的。如今在惶恐之下,把这些旧年的“隐情”和盘托出,以图减罪,也不难理解。 当然,她当时是否受到某些官员的“诱供”,以此作为攻击欧阳修的把柄,也很值得怀疑。当时、欧阳修等人发起了一场改革,史称“”,由此得罪了大批官僚。他们污蔑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并到处罗织罪名,一心要把他搬倒。 宋代文臣(剧照) 张氏爆的这段“猛料”,立即在朝野上下掀起轩然大波。政敌们纷纷攻击欧阳修是伪君子,连也要欧阳修给个说法。欧阳修当然矢口否认,并一再强调:张氏当年寄住自己家时只有七岁啊,自己就算再“风流”,难道会和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发生什么吗? 应该说这种反驳是很有力的。不料,从政敌阵营中跳出一个叫钱勰的官员,对欧阳修冷冷笑道:“七岁,不正是学簸钱的年纪么!” 听到“簸钱”二字,欧阳修立即明白他在说什么了,竟一时无言以对。 什么是“簸钱”呢?它是唐宋时在小女孩间流行的一种游戏,玩法非常简单:每人轮流抓一把铜钱撒在地上,以正面或反面的多寡决定胜负。钱勰提起的“簸钱”,出自欧阳修写的一首《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江南柳 从字面看,这首词似乎没有那么“污”,但稍有文学基础的人都能读出别样的意味。“柳”是经典的女性意象,而“成阴”一语双关,字面意思是树荫,却又暗示女孩的成熟。“江南柳”既然“未成阴”,就是说女孩年纪还小,于是“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人不忍攀折柳枝,黄莺也不忍站在嫩枝上唱歌。这两句互文见义,“人”与“莺”都指代多情的男性;“留取待春深”——既然年纪还小,那就等她长大再“下手”好了。 再看下阙。转眼女孩已是十四五岁的年纪,词人见她“闲抱琵琶”的样子,不禁回想她当年“堂上簸钱堂下走”的可爱情态。“恁时相见已留心”——那时候就已经对她有意了,“何况到如今”——何况如今她真的已到了“绿柳成阴”的青春年华呢。 读罢全篇,这就是一个“怪蜀黍”爱上“小萝莉”的故事嘛!女孩还是“簸钱年纪”,就对人家一见倾心,而且垂涎了好多年,一直看着人家从“叶小未成阴”长到十四五岁。虽说没有明写自己有没有“下手”,但光是这份心思就够让人侧目了。 这首《望江南》,选材独特而又略显“重口”,还有“簸钱”这样的细节描写,时间跨度好几年,怎么看都像意有所指。而张氏在欧阳修家住了七八年,出嫁时正好是“十四五”,难怪这首词越看就越像为她而写的。 由此一来,张氏是“人证”,这首《望江南》是“物证”,欧阳修差不多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尽管同僚和朋友们一再为他鸣冤叫屈,还拿出他的许多佳作证明他的文风一贯“飘逸清远,皆(李)白之品流也”,甚至否认这首词出自欧阳修之手,纯属政敌们的构陷,但都无济于事。 醉翁亭 不久,朝廷的处分下来了: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刺史。时隔千年,这场疑案的真相早已无从查考,但他在滁州写下的一篇文章却千古流传,这就是《醉翁亭记》。 好在,由于欧阳修的才华和政绩,没过几年他就被朝廷召回,最后是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死后还被追封为国公。这段疑案也就不大为人所知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