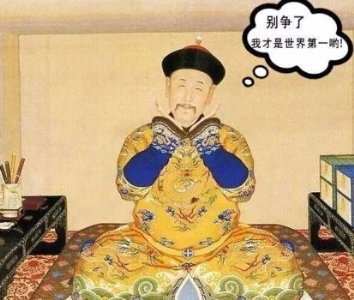电鳗的结构特殊能抵抗电流
大家说道电鳗会想起什么?加拿大电鳗吗?不不不,大家应该都会想到能放电的水物种,不光能放电攻击敌人,电鳗还能进行“远程攻击”,通常能在3米深的地方击昏鳄鱼。鳗鱼从哪里获得“高电压”?它怎么没被电击?
一种被称为“钠钾泵”的蛋白质在动物细胞中无处不在,其中的关键物质叫做ATP,每次使用ATP时,钠钾泵泵出3个钠离子和2个钾离子进入细胞,同时泵出一个正电荷。
对于大型动物来说,钾钠泵的重要作用是保持细胞内的钾、钠多、少的“静息电位”,保持细胞的通透性和体积,而且由于细胞两侧运动电位的存在,所以产生的电荷会相互抵消,所以不会产生巨大的电位差,也就不会有电流。但是电鳗体内有一种特殊的“电池”。它的一边有很多“钠通道”,但另一边没有。也就是说,钠离子在“电池”中是“单向”的,所以电池的两侧有一个稳定的电压。
虽然每个“电池”的能量非常少,但电鳗体内的“电池”数量太多了。“电池”就像“电池”、“串”、“并联”一样,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放电装置。电鳗能调节通过其神经的电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在充分释放电流的过程中,人体内的每一个“电池”都会被激活,发出大量电流。
根据资料显示,电鳗发出高电压300800伏时,其电流也非常大,一般在12安培之间,也就是说,电鳗的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000瓦以上,这样的“高压”足以电晕甚至杀死一条鳄鱼。那为何电鳗不能电死自己呢?由于电鳗鱼身体的电阻比水的电阻高得多,所以当鳗鱼放电时,他能控制自己的电流外泄,此外,它特殊的结构能防止内部器官触电。
吴王夫差缘何最后失败?战略重心产生偏差
最要紧的战略未必是最要命的战略;战略有重心,未必等于战略全面,的成败是一个典型的经营案例。图片来源于网络吴王在征战越国时受伤而死,嘱咐儿子夫差要报仇。夫差没有忘记父仇,后来灭亡越国,实现了自己对父亲的承诺,但接下来,他似乎陷入了骄傲自满的境地,成天荒淫作乐,忽视复仇的意志,最后亡于勾践。其实不然,夫差从来没有因为灭亡越国而志得意满,在那个时候,他的眼光投向了北方,因为灭亡越国根本不能提升吴国的档次,进入中原才是正道。这样做也是继承了他父亲阖闾的遗愿,当年吴王阖闾以和为参谋,向北挺进,一度灭亡楚国,只是因为秦国介入,以及国内发生兵变,才收兵回吴,称霸中原的战略意图半路夭折。夫差忘不了先王的战略意图,在“搞掂”越国之后,就继续北上。图片来源于网络所以,在勾践发愤图强的那些岁月,也是吴王夫差事业发展得最好的岁月,吴国的霸业半点也没荒废。公元前486年,吴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长江北岸修筑庞大的军事要塞——邗城,作为向北挺进的基地。接着,吴国又向北方的大国齐国发起大规模海陆攻势,吴国的舰队从海上绕向齐国的后方。对于这场海战,史书描述不多,它比古希腊著名的萨拉米海战还要早几年。经过数年的水路陆路攻战,吴国终于击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吴国和中原诸国在黄池会盟,实现霸主的梦想。然而,重点战略的实现,往往以牺牲其他战略为代价。夫差赌了一把,预料勾践一时没有胆量发起进攻,所以在后方只部署了老弱病残。结果勾践趁机水陆两路大军并进,攻陷吴都。当消息传到北方的黄池时,夫差杀了报信的使者——这样做是为了北方战略暂时不受影响。图片来源于网络夫差是个励精图治的人,但他没理清战略顺序。要实现重点战略有两条途径:一则是敢冒险,置要命的战略而不顾,先实现重点战略;一则先解决要命的问题,再解决要紧的问题。夫差走的是前者,他急于获得中原的承认。其实这两步棋都没错,问题是怎样掌握节奏。在发展事业时,轻重和缓急节奏未必合拍,次要的未必缓,重要的未必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产生严重的幻灭感是否是一种精神病变?
中国古代精学不发达,对心理疾病缺乏了解。因此,对某些人暴戾乖张的行为,常常用性格偏执,缺乏修养来解释,极少有人能想到这也是一种精神病变。用现代观念来看下面这桩奇案,就不难得到一个答案:晚年的在心理上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明太祖晚年编撰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奇案。此案之所以称为奇案,是因为朱元璋对此案的处置方法:医生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便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后,又要其交待解毒之方;并用粪清兑凉水为其解毒,直至次日方枭首示众。在“服毒及其反应”的测试中,年老的朱元璋反而更像一个的科学工作者,他不但认真地记录了服毒者在神态上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反应,还高度关注其临近死亡时的心理活动。整段文字描述得绘声绘色,以致朱元璋事后回忆时,仍是那么兴致盎然,回味无穷。 网络配图 用以上案例来分析朱元璋的晚年心理,使人感觉到,这个以铁腕治理着大明天下的布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其行为也让人觉得越来越反常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晚年的朱元璋产生了越来越重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老年的到来,朱元璋突然间意识到了“帝力之微”的无奈。譬如:他用重典治国,用铁腕反tan,而且一度坚信只要大明王朝按照他所确定的轨道运行,就一定能“复先王之治”,自己就能成为一个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然不那么乐观了。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故意贬低自己是“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这样悲观的情绪发生在自起兵以来就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朱元璋身上,是不可思议的。 太子的早逝,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不能不说是致命的一击。他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一边大哭,一边悲叹:“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在群臣面前大哭,毫不遮掩地表现出自己软弱的一面,这对于朱元璋来说也是罕见的。 太子死后,衰病中的朱元璋下诏征求善于预测未来的术士,“试无不验者,爵封侯”。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说明支撑朱元璋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了。对于一个处在迷茫之中,又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来说,是最容易因被焦虑所困扰而变得,暴戾乖张的。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仅仅是幻灭感,还有一种因患得患失而产生的忧虑感。 网络配图 因为明太祖希望,费尽,好不容易打下的朱明江山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因此,沉重的江山就背在了明太祖的身上。虽然他相信,在他,无人能撼动这座大厦的根基,但在自己撒手西去以后呢?由于皇太子早逝,他选择的是太子的儿子做皇位继承人。由于皇太孙的年幼柔弱,这就更加重了朱元璋担心江山在他身后一朝易主的心理负担。 于是,为了确保朱家天下不被易主,朱元璋必须与时间和死神赛跑,抓紧做好最细致的防备工作。一方面,他除了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为确保江山无虞而地工作外;还要为了清除隐患,不惜大开杀戒。另一方面,朱元璋也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在有生之年,替后代把危及朱明江山的所有漏洞都堵上。这就使得年老的朱元璋愈发焦躁不安了。 在幻灭感和忧虑感的双重重压下,晚年朱元璋的暴虐与攻击性达到了极致。他对臣属方信又疑,才赦复罪,让人不知所措;就是其嫔妃,即诸王子的母亲,也常常会成为其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据清人查继佑的《罪惟录》记载:在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乃亲自处死胡充妃,并弃尸郊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而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妃、伊王之母葛胡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朱元璋怒气平息,想用棺木重新安葬时,尸体早已腐烂得无法辨认,只得堆了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了事。 网络配图 史书在记述朱元璋的晚年生活状态时,有这样两句:“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一个时时担心江山易主,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稍有风吹草动,就彻夜不眠,惶惶不可终日的老年皇帝,怎么可能不产生心理变态呢?而这种变态的心理,往往会驱使他去用一些常人难以理喻的暴虐行为来纾解他的焦虑情绪,从而得到某种病态的心理满足。就像亲自观看服毒者的垂死挣扎一样。 一个一生都在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手中的权力,而不懈努力的皇帝,在幻灭感和忧虑感的重重压力之下,怎能不会变得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甚至逐步发展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变异呢?由此想来,对于晚年朱元璋一些有悖常理的怪戾行为,除了憎恶以外,往往还会使人生出些许的同情和怜悯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