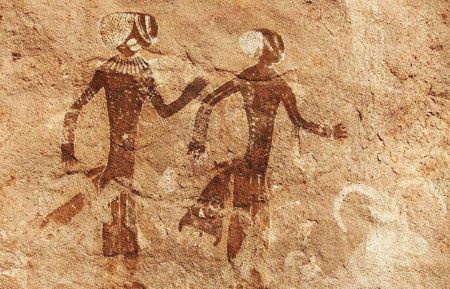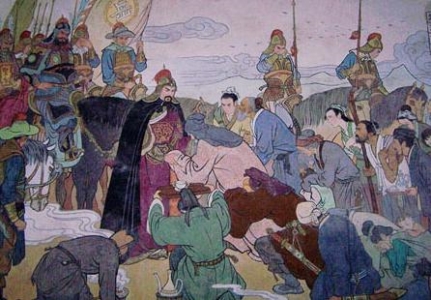杨恽在大众中的知名度不高,要谈他,就要先拉出他的家世来矜夸一下。
他是汉昭帝时丞相的儿子,更是的外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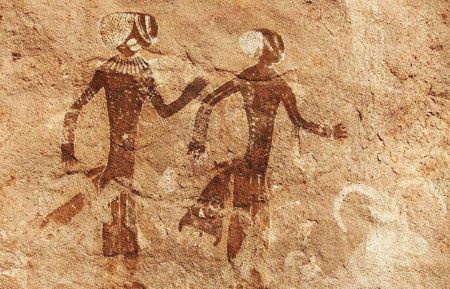
作为丞相的儿子,司马迁的外孙(虽说通常外孙这样的旁支很少沾得上光了,但宣帝时曾迁杨恽来阐述传播其外祖父的书,时又封司马迁的后人,说明司马迁地位已经很超然了;又因被宫再无子嗣,故其女儿的旁支也可继爵),杨恽以才能著称,好结交,早就名显朝廷了。
可以说,司马迁《》得以传播流传,杨恽是有很大功劳的。
揭发谋反让杨恽得以封侯;还有两件事,都增加了杨恽的好名声:一是废止了郎官出补外官要出钱的“山郎”贿赂制度,二是,父亲的财产都分给宗族,后母给他继承的财产他也全部分给后母的昆弟。
他廉洁无私、处事公平,都是人人赞誉的。
然而,杨恽性格中有致命的短板。
按木桶定理来说,就是他最糟糕的一面决定了他人生的命运。
《汉书》中云,“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
”再有才能再慷慨,天性记仇又阴毒刻薄,无论如何也是不讨人喜欢的。
这就种下了恶果。
与杨恽有过节的太仆戴长乐的下狱是一个导火索。
戴长乐曾奉诏摄天子事,在宗庙演习礼仪,回来他就大剌剌地对掾史说:“我亲自面见受诏,而且还是秺侯坐在副帝的位置上御车。
”结果这番话被人告上去了,称其“非所宜言”。
戴长乐怀疑这是杨恽让人上告的,也上书告杨恽。
杨恽犯了大多的罪呢?其实也就是和戴长乐一样,老是说一些不得体的话。
一桩是当初高昌侯董忠的车奔入北掖门,杨恽就对人说:“听说以前有奔驰的车撞到殿门,门关折断马也撞死了,没多久昭帝就崩了。

现在又是这种情况;看来这都是天命啊。
”一桩是单于使者的信在朝中被遍示群臣、大家在讨论匈奴会不会来朝的的时候,杨恽又乌鸦嘴了:“单于得到的好吃好用的,称其‘殠恶’,显然对汉朝没兴趣,看来是不会来了。
”一桩是杨恽看着西阁上画的帝王图,指着、纣对旁人说:“天子如果经过这里,问一问这两个人的过错,就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训了。
”一桩是听闻匈奴降者道单于被杀了,杨恽说:“碰上一个坏,大臣的好建议都不用,自己也会被搞死。
秦的时候任由宦员乱政,诛杀忠良,所以走向灭亡;如果好好能任用大臣的话,政权就能延续至今了。
古代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还有一桩,是曾说过:“正月以来,天阴不雨。
我猜,天子今年肯定熬不到去河东祀后土祠的时候了。
” 这样的句子我勉强翻译出来,多数仍然很难理解有什么问题。
戴长乐上书在列举这些“罪证”的时候,是有几句评论的。
比如,西阁上画的人明明有尧、舜、禹、汤,你为什么不称这几个好帝王,偏偏以桀、纣为例呢?你安的什么心?比如,你引用灭亡的故事来映射今天,诽谤今上,想不想活了?比如,你猜皇帝活不长了,把皇帝编进段子里,更是悖逆绝理! 对于这样的逻辑,我无法反驳。
杨恽那张嘴是比较不经大脑,说话难听,然而,都是私人场合,造成什么坏影响了吗?都是评论而非谣言,煽动出什么恶果了吗?即便有罪,又能罪到哪里呢? 其后,杨恽并不认罪,希望找人作证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结果还没成功就被宣帝侦知了,又成了一重罪。
结果,杨恽的罪名被编派得非常严重:“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訞恶言,大逆不道。
”宣帝不忍杀他,就把杨恽和戴长乐都免为庶人。
因为有昭宣的中兴,一般史书对宣帝的评价颇高。
然而,当其太子委婉地劝他刑罚请不要太过份的时候,宣帝就生气了,认为刘奭“柔仁好儒”,发出那声著名的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从根本上来说,宣帝就是另一个武帝,杂糅,,猜忍刻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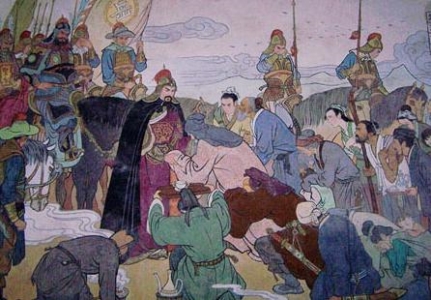
事实证明,宣帝并没有放过杨恽。
杨恽没有了爵位,就开始在家里治产业,起室宅,大手笔地挣钱花钱,自娱自乐。
他的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劝他,大臣废退之后,就应当闭门反思,夹着尾巴做人,不应当那么高调,更不能四周结交宾客。
杨恽哪里听,写了一封《报孙会宗书》,洋洋洒洒,反驳了他。
信中云: 我犯这种错啊,夷灭都不足以塞责了,没想到还不杀我,都是圣主的功劳啊。
我反思自己,应该作农夫过日子,所以才率领妻子儿女戮力耕桑,以供给朝廷的赋敛。
没想到就这样还有人不满!我现在已经是农民了,辛苦耕种;咱俩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也别再用卿大夫那一套来要求我了! 于是,有人上书说,现在的日食,就是因为有杨恽这种坏人的存在——结果,杨恽下狱。
这就是欲加之罪,连理由都懒得编了。
加上前面那封《报孙会宗书》,杨恽被判大逆无道,腰斩。
《汉书》说杨恽阴毒害人,并无实事,惟见他脑子拎不清,老是乌鸦嘴。
可是,谁说了乌鸦嘴是要处死的? 就这么一个开明的地方,一位开明的君王,那里的臣民,会因为说了风凉话就被腰斩族灭。
我们却称之为中兴,不吝赞美。
那么,我们当然会欢迎更多的言论入罪;即使律例里已没有没有腰斩族灭之刑了,我们还有其他言论罪侍候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唐太宗李世民夺下隋朝江山是一次成功的抄底
于公元613年东征高丽,押粮官杨玄感欲发动兵变,请来好友李密做参谋,李密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封死隋炀帝东征的归路;中策,西取关中,观望天下;下策,攻取龙头股洛阳。而文武双全的杨玄感却选中了下策—— 杨玄感“斩仓”不彻底兵败身死 杨玄感长途挺进洛阳。6月初才发布文告起兵,到6月中旬,前锋居然已杀到洛阳宫城的太阳门。可事实证明,杨玄感确实追高了! 洛阳城确实是百官家属所在地!可正因为是太太团所在,隋朝将士才焕发出高昂的战斗激情。洛阳守将樊子盖死守城门,杨玄感轮番猛攻,就是不进球。拖得久了,隋朝的前锋、中场、后卫都回来救洛阳这个大球门。东征高丽的前锋不等隋炀帝下命令就回兵救场。东征总队长隋炀帝也紧急回到涿郡(今北京),坐镇指挥。 更恐怖的是,杨玄感当初以为他起兵,天下会响应,结果除了一些草莽英雄落魄子弟,天下郡县级别的地方政府无一个响应的——隋朝的行情虽然下滑,但还没下滑到底部,所以他振臂一呼,响应他的只有回音。李密劝告:“咱们快快斩仓吧,放弃龙头股,去关中。” 上苍总是很耐心地给人一个又一个机会,杨玄感放弃了龙头股,解除对洛阳的包围,降低仓位,转向西边发展。 然而,军队经过弘农郡时,当地的百姓拉住杨玄感的马头,苦劝他取下弘农再西行。杨玄感也想在彻底斩仓前再获取点利润。因为弘农郡有优质资产:粮草。于是杨玄感留下来攻城,天下大盘瞬息万变,岂容得你贪恋那么一小点盈利?这点盈利很可能是市场留给你的毒丸。杨玄感才离洛阳,又因弘农被套牢。隋朝各路大军,围住这位仁兄一阵狂殴,杨玄感请人杀死自己,然后被隋军剁成肉酱烧成灰烬,满门抄斩。 这是第一个追高者杨玄感的可悲下场。杨玄感追高追死了,但上天还是再给了一次机会,当然不是给杨玄感,而是给了杨玄感的残余势力:李密。 李密为何走上杨玄感追高的老路? 李密当时也被捕,但机智的他逃脱了。公元616年,当远在山西太原的李渊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起事的时候,李密认识了王伯当,王伯当把他介绍给了瓦岗军头领翟让。李密投靠了瓦岗军这家大公司,并交出漂亮的业务单:616年10月27日,李密精心设计大海寺伏击战,击杀隋朝名将张须陀。凭这张业务单,李密渐渐掌握了瓦岗军这家公司。有了资本,有了业绩,李密下一步剑指何方?居然还是洛阳! 理由:洛阳是龙头股,多粮仓,而天下人正处于饥饿当中。攻下并打开粮仓,有了粮就有了人,百万大军一夜可成。拿着隋朝的资本跟散户们分红,自己不出本钱,又能聚集散户人心,?617年2月,瓦岗军攻下洛口仓,散粮给百姓。 此时,太原的李渊尚无动静。李密在盈利的道路上,远远跑在李渊的前头。有杨玄感的教训在前面,李密为何选择了自己制定的下策呢? 李密自己给出了答案。公元617年的5月,大概是李渊父子在太原起事前后几天,柴孝和建议李密派兵驻守洛阳四周,然后从高仓位风险中脱离出来,夺取关中,走稳健盈利之路。李密说:“这是我当年精心考虑过的,但是我的手下都是东部人,如果洛阳不拿下来,分不到红,谁愿意跟我去西部?” 从此,李密也走不出杨玄感的怪圈,被洛阳套牢。当时镇守洛阳的是越王,天下各路援军都来支援龙头股洛阳,于是,来了,成为李密的劲敌。 这时候的李渊父子趁着洛阳鏖战,从容在太原起事,夺取关中。李渊父子也将目光投向了龙头股洛阳,李密王世充正在鏖战,洛阳城布帛堆积,都用来当柴烧。当时的布帛有货币的功能,洛阳城在拿着货币当燃料用。看样子似乎可抄底了。 公元618年4月,来抄底了,打的是救援洛阳的旗帜。可李世民在洛阳周边观望一番,发觉抄底时机未到,于是决定:撤!看清历史底部就是看清历史大势,哥真牛! 李密和王世充在洛阳城周围耗。而形势已变化:李渊父子走了李密所制定的中策之路,占据山西陕西,西进的路线不复存在。李密既然已经走在下策的路上,该如何挽回?走错了第一步,但第二步正确,事情还是可为的。 王世充的“一顿早餐攻势” 此时,李密最经得起消耗最优质的资本就是粮草。他拿着这个分红,召集天下人来效力。凭着自己雄厚的资本跟对方比烧钱,谁的钱先烧完谁就先退出市场。 王世充手中粮草越来越少,又屡次被李密击败,眼看着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当时投靠瓦岗军的看准了这一点,建议说:“挖好壕沟,筑好城墙,王世充粮草一尽,他就玩完。”李密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读史书有个经验,如果史上有人提出挖好壕沟,不与敌人交战的策略,那绝对是上上选。胜仗不一定是打出来的,可能是熬出来的。 然而,瓦岗公司糊涂人多过清醒人,清醒的少数人拗不过糊涂的大多数人,还得顺应糊涂的大多数。李密是清醒的,魏征是清醒的,然而瓦岗军大多数指挥层是不清醒的。以猛将单雄为代表的一大帮糊涂蛋叫嚷着形势大好,三天就痛灭王世充。李密无奈,只得放弃只守不攻的策略,做出了主动进攻的态势,走上高仓位操作的路线。 而此刻的王世充也提高仓位,高风险操作。同样一个措施,在王世充这里却是正确的:反正粮草不多了,静守绝对蚀本,一博还有翻本甚至博大的机会! 暂且把王世充军队发动的攻势命名为“一顿早餐攻势。”618年9月12日清晨,王世充部队就在床头吃饭,喂饱战马,忽然奇袭没有防备的瓦岗军。这帮江淮老兵,肚子里一顿正在消化的早餐是他们唯一的资本,却支撑着他们玩命。王世充事先准备好一个与李密长得很像的人,绑在马上,然后牵出来宣告说:“李密被我们生擒啦。”瓦岗军在王世充的“一顿早餐攻势”前崩溃,此战史称“偃师之战”。李密手中资本几乎丧失殆尽,然后投靠李渊,最后,因为受不了李渊的傲慢而密谋造反,被李渊所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湮没在历史深处的大汉奸吴三桂谋士:不为人知的大汉奸吴三桂
一生在、大顺朝和诸政权之间投机取巧、反复无常,堪称明末清初的大阴谋家。然三桂极善笼络人才,身边聚集了大批谋士为其效命,这些淹没在历史深处的阴谋家背后的阴谋家,在三桂反清的过程中推波助澜、出谋划策,在滚滚东去的历史长河中搅起朵朵浪花,亦不失为一景。 1、在吴三桂的众多谋士中,方光琛、初二人堪称智囊。方光琛是明朝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善谋略,早年曾与吴三桂缔盟为忘形交,后亡命至云南,入吴三桂幕。方光琛为三桂心腹,深受赖,可谓首席谋士。三桂谋士中最具战略眼光的当属刘玄初,刘玄初原是大西农民军刘文秀帐下幕客,刘文秀兵败后转为吴三桂谋士,此人极具大局观,眼力深邃,可惜他的很多谋略并未被三桂采纳。 2、吴三桂受封云贵后,势力恶性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引起了清廷的极大不安。帝亲政后,鉴于历史上的藩镇之祸,更是认为吴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三藩不可不撤。康熙十二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尚可喜申请撤藩实际上是害怕位高权重引起朝廷怀疑,最终招来祸事,故以此保全声誉,以求善终。康熙抓住这一难得时机,,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假意上疏朝廷,请求撤藩,以试探康熙帝态度。对此,刘玄初极力进行劝阻,提醒吴三桂不要自己陷自己于被动的境地,“上久思调王,特难口,王疏朝上而夕调矣。彼二王辞者自辞,王永镇云南,胡为效之耶?不可。”(皇上很久就想把您调离云南,但特难开口。您上疏,一定会朝上而夕调。尚、耿两王愿辞就让他们辞去,您可永镇云南,为什么非要效法他们呢?您不可上疏!)但吴三桂并没有理会刘玄初的劝谏,反而气冲冲地说,“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我马上就上疏,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由于这件事,三桂迁怒于刘玄初,让他外任盐井提举。 结果正如刘玄初所料,康熙帝顺势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办理撤藩事宜,由此证明了刘玄初的远见卓识。“未几,有贵州之变,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学士”,很快又把他召了回来。吴三桂还在内心深处始终幻想能与康熙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但谋士们却远比他清醒,方光琛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顿生反义。为此,三桂决定先找方光琛筹划。平日,吴三桂待方光琛甚厚,每有余暇,二人经常评论世务,很是融洽。吴三桂第一次找方光琛时,没有明说造反;第二次谈话才说出本意,但方光琛不置一词。第三次,吴三桂天刚亮就登门问计。方光琛见吴三桂反意已决,即为三桂分析天下形势,指出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可传檄而定,其余战胜攻取,易如反掌!于是吴三桂决计起兵。由此可见,在举兵造反这件大事上,方光琛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起兵之初,吴三桂群集众谋士问计,刘玄初分析道:“明亡未久,人心思奋,宜立明后,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矣”!建议拥立明朝后裔以争取人心,号召天下。而方光琛则予以反对,“出关乞师,力不足也,此可解(指当初献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事);至明永历已窜蛮夷中(指南明永历帝在吴三桂大军的追击下逃入缅甸一事),必擒而杀之(指吴三桂进攻缅甸,迫使缅甸献出永历帝及家属一事),此不可解矣。篦子坡之事可一行之(指吴三桂在篦子坡杀害永历帝父子),又再行之乎?”方光琛的话击中了吴三桂心中的痛处,三桂遂不用刘玄初计策,决定自立为王,号令天下,事实证明三桂这招棋完全是一个昏招。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验证了刘玄初的预想,吴三桂打出了“大周”年号,显无恢复明室之图,失人望于天下,前明反清势力便不愿与其合作。当时著名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指出,“世乏,托身焉所保”?吴三桂由此失去了无数相助者,着实可叹可惜。 4、反叛之初,吴军,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倒戈投吴,曾经的清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皆不敢战。就连北京也出现了杨起隆起义事件,京师亦,人心惶惶。一时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至康熙十三年三月,吴三桂已拥有云、贵、湘、蜀,并深入到湖北巴东、宜都等地。襄阳总兵杨来嘉投降后,江北亦为之震动。 然而吴三桂打到长江边,举足即可渡江,却“至夷陵,驻兵松滋,三月不进。”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将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对于吴三桂的停顿不前,吴军的将领、谋士们甚是诧异。原来吴三桂打算以此逼迫清廷放还世子,并与之议和划江而治。为此,吴三桂给康熙写去一封信,交给被扣留的礼部侍郎折尔肯和翰林院学士傅达礼,释放他们回去,转呈康熙。 刘玄初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写信劝告吴三桂,“愚计此时当直捣黄龙而痛饮矣,乃阻兵不进,河上消摇,坐失机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为何说也。意者王特送诸大臣入朝为王请乎?诸大臣辱国之臣,救死不暇,乌能为王请也!若曰待世子归乎?愚以为朝廷宁失四海,决不令世子返国也。夫弱者与强者斗,弱者利乘捷,而强者利于角力;富者与贫者讼,贫者乐于速结,而富者乐于持久。今云南一隅之地,不足当东南一郡;而吴越之财货,山陕之武勇,皆云翔猬集于荆、襄、江、汉之间,乃案兵不举,思与久持,是何异弱者与强者角力,而贫者与富者竞财也?噫!惟望天早生圣人以靖中华耳。” 刘玄初的信直接点出了当时的形势和吴三桂的顾虑,希望吴三桂做“圣人”以恢复汉家天下,告诫三桂以云贵一隅之地对抗中央,利在速战速决,长久对持势必自取灭亡。但这封信依然没能打动吴三桂,“未几,玄初郁郁而死”。刘玄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他在康熙势必要撤藩,拥立明朝后裔以争取人心,以及吴军战略部署等方面的见解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他对康熙的想法、举动可谓。可惜吴三桂并不采纳他的建议,事实上,吴三桂没有真正的雄才伟略,也就是一个阴谋家。除了刘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其他谋士、将领也提出了“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出巴蜀,据汉中,塞崤函自固”等主张。这些主张各有侧重,但从战略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力主进兵,决不能停顿下来。可惜吴三桂一概不听,就是屯兵不进,由此坐失机宜,给了清廷喘息的机会。吴三桂最终的命运,至此已经注定了! 5、自刘玄初死后,吴军无人再敢在三桂面前提出北进的建议。而稳住了阵脚的康熙帝开始从容调度,迅速展开反击。结果正如刘玄初所料,丧失战略先机的吴军很快陷入了窘境,三桂亦在绝望中病死。直至吴三桂死后,勇将吴国贵才敢指出吴三桂此前的战略失误,“从前所为皆大误也”,“宁进而死,不退而生。”然而此时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呢?康熙二十年十月,清军攻克昆明,吴三桂吴世璠自杀。三桂首席谋士方光琛束手就擒,被凌迟于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标签: